由上海儿童文学作家陆梅创作的小说《像蝴蝶一样自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以创作了《安妮日记》的德籍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和上海女孩老圣恩跨越时空的一场心灵漫游展开故事。《安妮日记》记录了安妮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两年的密室藏匿生活,以及其对战争、和平、爱情、亲情的思索,成为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二战文学作品”。小说《像蝴蝶一样自由》对安妮形象的征引与再创造不仅勾连起安妮个人记忆与犹太难民的“上海记忆”,亦架起中德文学文化互鉴之桥梁。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这部创作于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的文学作品,其价值愈显深远——它不仅启示中国少年儿童铭记二战历史、珍视和平,更为中德文明对话交流注入了文学力量。2025年7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方心怡就小说《像蝴蝶一样自由》采访了陆梅。

陆梅,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作品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德国慕尼黑“白乌鸦奖”等
“安妮自然而然地跳出来了”
方心怡:小说《像蝴蝶一样自由》中,生活在平行世界的安妮虽有一副犹太少女的面庞,但却会讲中国话,也了解中国儿童的生活与苦闷,可以说,您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中国的安妮”。那您是如何想到去构建这样一个人物的呢?
陆梅:我可以先说说触发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灵感。那时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去杨树浦水厂,有心想去看看水厂边的博物馆。我们在栅栏外瞧见水泥新封的门和红屋顶房子满墙的爬山虎,不见一个人,时间像是停滞了。门口有个大叔值班,被告知博物馆周末不开放。然后我们第二回又去,那天是星期四,正好女儿学校放假,到了水厂外又被告知博物馆不开放。在那样一个状态下,我女儿,一个小小女孩往铁门里揪了一把飞蓬草,一股脑往铁门里扔。在她肆意发泄着不满的时候,我眼前的那扇水泥门好像突然开了,还有一整面墙的爬山虎也纷纷张开了耳朵,一个世界打开了。所以,小说中老圣恩脑海里的念头就是当时我的想象。水厂很容易让人想到地下的事情,后来我把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中特莱津集中营里那么多孩子的画勾连了起来。这个故事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安妮自然而然地跳出来了。我希望有一个和老圣恩惺惺相惜的女孩,安妮就这样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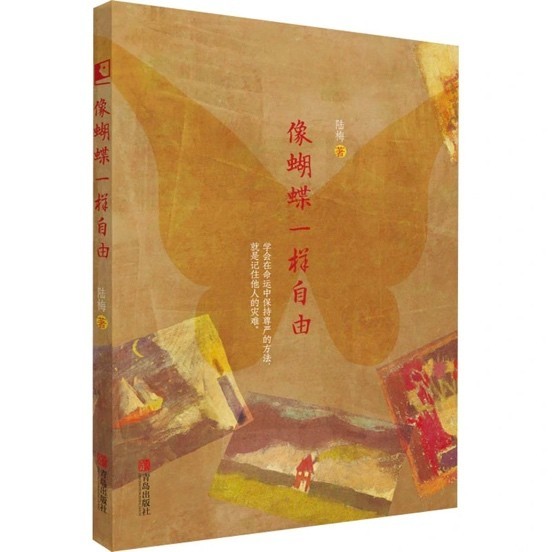
这个女孩深褐色卷发,眼睛大而且黑,脸清瘦苍白,和电影里的安妮没啥两样。她在我脑海里,永远生活在13岁。自然而然,这两个女孩要相识、要交流,要有一个释放,通过小说的形式,她们可以更酣畅淋漓地探讨一些浩大命题,但又跟两个女孩的切身处境相关。
如果你说小说中的安妮是“中国的安妮”,从你的这个研究角度,我是认可的,但是从我的创作角度,我确实没这么去想过,我就想让这个女孩有机会和一个中国女孩相识相会,自然而然的她要会中文。在小说的逻辑上,她就是一颗老灵魂,她没有国界,可以和老圣恩深度交流,也没有语言障碍。

安妮·弗兰克
方心怡:那您又是如何想到将其与犹太难民的“上海记忆”以及特莱津集中营的儿童勾连在一起的呢?
陆梅: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将安妮的命运跟中国的上海勾连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而且这是必须的,否则你写这个小说的场景、背景就不成立。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一部分历史事实的话,那就成一部架空小说了。
要让安妮和老圣恩在某个场景下相遇,然后这次相遇又得跟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勾连起来,在我脑海里,霍山公园是一个理想之地。小说中,老圣恩从霍山公园进去,看到了盛放的彼岸花,然后才到了安妮和特莱津集中营的孩子们“灵魂的居所”——金房子。
关于安妮和特莱津集中营的儿童们,我在小说前言中提及,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给了我最初的心灵触动。这本书是写特莱津集中营孩子们的命运的,小说之所以取名《像蝴蝶一样自由》,也是向这本书致敬的意思。小说里,老圣恩问安妮;“我记得你好像是在贝尔森集中营,怎么会认识特莱津的孩子们呢?”我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作为一个真真切切的游魂,安妮身陷黑暗的深渊,不知道哪里是出口,她徘徊在漆黑巷道里,迷惘又恐惧。然后她听到一个声音,一个亲切的女声,这个声音说:“安妮,不要跑,魔鬼只在你的意念里,你不怕就没有魔鬼……”这个声音就是女艺术家弗利德。弗利德是特莱津孩子们的艺术老师,自然而然的,特莱津和安妮有了连接。
还有比如中秋节的晚上,老圣恩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金房子里那些来自特莱津集中营的孩子们,他们也忍不住在小册子上写下自己家人的名字。这个情节的灵感来自我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看到的一整面的名单墙。当年我去那里参观,驻足在这面墙前,无比震撼。
阿姆斯特丹的密室与鼓浪屿的金房子
方心怡:您在构建金房子的时候,是以“后屋”,也就是安妮的密室为原型吗?我发现它们的构造很相似,比如安妮房间的位置,大厨房的位置;又比如,金房子里,安妮房间的墙壁上贴有许多特莱津集中营儿童的画,而安妮在密室房间的墙壁上贴了她喜欢的明星的照片;再比如,密室和金房子的阁楼里都有一扇窗。
陆梅:你这么联想我很高兴。但是我写作的时候,金房子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脑海里并没有这个密室。但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潜意识。我当初脑海里泛起的是实实在在的想象——是我在鼓浪屿一次游走时看到的一幢房子。在鼓浪屿,那样的房子还是挺多的,有台阶、庭院,上面三层、两层的那种老房子。因为安妮是一颗老灵魂,我就觉得她应该是在地下室,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就是说,金房子的地下室是我想象中的,实际未必有。说到密室,我从没去过荷兰的安妮之家,也没有认真研究过密室的结构。但是《安妮日记》就是在密室里写成的,它进入我脑海倒也必然。
小说写作的神妙之处是,写作者自己不自知,可是当他创造出来,不承想和现实有了呼应,这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奖赏。可见所有的意识和潜意识,确实会激活深藏在你脑海深处的那部分“储备”。文学中的现实和生活中的现实的关系问题,有时是超越,有时是印证,有时互相生发,有时互为镜像……很难说一定是前者高于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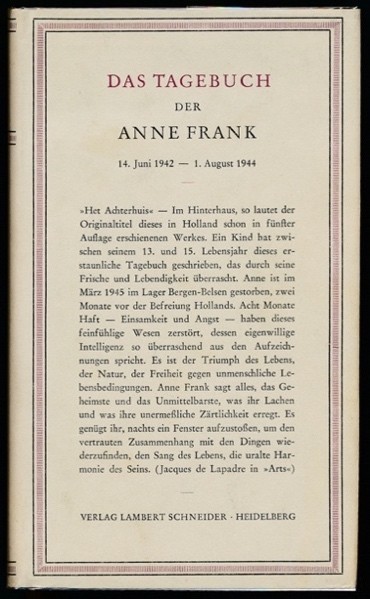
德译版《安妮日记》
方心怡:那彼岸花是否可以视作召唤“幽灵”安妮的一个媒介呢?或者说,暗示读者安妮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彼岸花它连接生死,也就预示着安妮她其实不存在于老圣恩生活的真实世界之中,而是在生死之间、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第三空间。
陆梅:彼岸花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如果没有彼岸花的话,光靠老圣恩自己脑海里的那种“想要消失一会儿”的念头,还是很难和在地下城堡的安妮联结起来。老圣恩在白日梦中与安妮相见,但她终究要回到现实中。如果没有召唤的一种象征物的话,好像不行,所以我想到了彼岸花。
彼岸花是一种很特别的花,书中也写到了,它比较多长在山野墓地边。花呈放射状,一丛丛一簇簇,放眼望去,像是着了魔,红得像火一样。小说中,我把彼岸花安排在霍山公园。实际上当然霍山公园里没有彼岸花。彼岸花就是一个召唤之花。
“安妮站成了一棵树”
方心怡:您在小说里提到,老圣恩10岁之后就见不到安妮了,10岁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陆梅:写到安妮和老圣恩要分开的时候,我想要给她俩找一个更合理的离别方式。对一个孩子来说,她不太可能是突然之间告别童年的。我希望有一个仪式,或者是一种提醒和暗示。老圣恩写过一篇小作文《十岁的树》,她提到9岁和10岁最大的区别,就是10岁是两位数,一个人要活过两位数并不容易。你看99是两位数,但人一般不太可能活过三位数,老圣恩就觉得9和10是一个跨界。那么我想10岁和11岁,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孩子年龄的暗示,具体小说里写到了,就是一种童年的告别,一个长大的提醒。
方心怡:在小说中,您写到,安妮站成了一棵树,金蝴蝶飞来停在了安妮身上。安妮与自然的这种融合又有什么含义与作用呢?
陆梅:安妮站成了一棵树,也是受老圣恩这篇作文的启发。另外,那些金色的蝴蝶是有隐喻的。林达在《像自由一样美丽》里提到特莱津集中营的孩子创作的诗《蝴蝶》,所以蝴蝶的意象很重要。蝴蝶的来和去寓意着它们的自由和飞翔,向着明亮那方的追求。蝴蝶的来,也是一种接引,那种接引对安妮来说是灵魂和灵魂的呼应,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写到那一刻,她自然而然的就站成了一棵树。
方心怡:您觉得女孩和树之间有什么相似的特质吗?您也曾提到,您对树、对自然有特别的情愫。
陆梅:有很多。你看我还写过一本散文书《刷着阳光的树》,指的就是那些即将告别童年的男孩女孩们,他们就像是一棵棵白桦树,刷着阳光,翻着亮片,充满了蓬勃的生命气息。所以赋予少男少女以树的形象,在我这里是自然而然的。我甚至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在小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找到一棵自己的树,然后和这棵树休戚与共、共同成长,那真是人间最美好的童话。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