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秩序瓦解之后,可能转向新的有共识的霸权秩序,也可能转向破碎化、冲突的非霸权秩序。在前一种情况,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与霸权的世界经济相容;在后一种情况,由于没有出现一种通行的世界经济模式,因此各国的模式、各国实现积累的社会形态都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在非霸权周期, 各种模式之间的竞争会加剧。
制度的比较
由于旧霸权已经失去了统摄力,各国内部的秩序也开始动摇和瓦解,世界也就失去了一种通行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先完成国内霸权重构的国家,将在国际模式之争中占得先机。如果这个国家实力超群,则将成为新的霸主,将内部制度推广到国际上。因此在霸权转换的过渡时期,各种模式之间的竞争将会加剧。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内部发展动态、制度特点,成为西方高度关注的对象。
2014年,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Lawson)提出了一个不同发展模式的分析框架: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竞争性威权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官僚资本主义。而这四种模式之间的不同是国家角色的大小。自由民主资本主义鼓吹市场作用,限制国家作为,施行民主;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尽量平衡市场、国家与民主三者的关系;竞争性威权资本主义则倾向于国家控制市场,同时限制民主;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拒绝民主,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难以判然分开。 这四种模式中,前两种可拢括称为“民主资本主义”,后两种可拢括称为“威权资本主义”。
这四种模式,是为了便于论述和比较而构建出来的理想模型,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国家,且现实情况也在不断变化。布赞与劳森认为, 大体而言,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英国血统的国家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欧陆大部分国家、南美、日本、印度和韩国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俄罗斯、伊朗、坦桑尼亚、肯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属于竞争性威权资本主义,一些亚洲的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大部分海湾君主国以及一些中亚国家则属于国家官僚资本主义。
四种模式各有优劣。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先锋,金融与债券市场最为发达,受危机冲击也最大。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向新自由主义转型之后,工人的工资上涨幅度受到了抑制。为了提升民众的购买力,信贷业发展起来,民众借债购物、 借债买房成为常态。如果房价能一直保持升势,且通胀和利息都能保持稳定,这种情况倒也无所谓,民众确能获得实际好处。但是一旦通胀率增高, 银行随之上调利率,买房的人就会减少,而手里有房的人将面临双重压力:房产价格下降、还贷金额增加。到了一定程度,楼市崩盘,楼市背后的金融风险爆发,便就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方式多为控制通胀、削减政府开支,外加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但这种方法如要起效,就必须同时配合经济增长,否则就会加剧贫富分化。
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相比,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中的“社会”成分更为突出,也就是说,更强调社会整体的福利与责任。在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的角色更为突出,不但亲自引导产业发展,还要负责为民众提供福利。通常说来,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危机多、风险大、不平等严重,但增长快、 就业率高;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则正好反过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欧陆国家)因为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关系紧密而受牵累,自身也陷入危机之中。在德国带领下,欧元区主要以紧缩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政策,甚至比美、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与美、英相比,欧元区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而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更低,因此紧缩政策对欧元区所带来的冲击更大。
竞争性威权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选举,但因达不到“公平、公正、公开” 的选举标准而仍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异类。这些国家通常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推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管控相对严格。不少国家既保持了政治稳定,也实现了经济增长。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竞争性威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表现总体优于民主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而且应对危机的决策更为迅速有力。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并未削弱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的优势。东欧国家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在2014年7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今天,世界试图去理解那些非西方、非自由,甚至非民主,却非常成功的国家。”他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已经不能保持全球竞争力”,并表示匈牙利要建设“非自由民主”国家。此番讲话震动了西方世界。
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对海外资本开放,市场有活力,也有表现不错的本土企业,但与此同时国家在市场中扮演突出角色。竞争性威权资本主义和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也有缺陷。在施行这两类模式的国家中,官商太近,易生腐败;由市场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多元化的活力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疏导;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甚至甚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
重估“欧洲模式”
竞争性威权资本主义和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强调国家的功能,力图在现有条件下以国家之力引导资本、聚集资本、发挥资本的战略潜能。这种做法在全球竞争中优势渐显,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到了广泛关注。
欧盟委员会曾在2010年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当欧洲需要解决它自己的结构性弱点的时候,世界已经快速前进,十年后将是非常不同的面貌……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正在加剧。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正大力投资科研技术以助其产业爬升价值链、‘跃’入全球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2012年曾推出特刊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称“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遭遇危机之时,新兴市场中崛起了一种新的、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
到了2024年,欧洲的紧迫感更强了。这一年,欧盟邀请两位“老领导” 领衔撰写了两份关于欧洲竞争力的重磅报告,并将这两份报告作为欧盟改革的重要参考。第一份报告是意大利前总理莱塔(EnricoLetta)于当年4月公布的《不仅仅是市场》。第二份报告则是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MarioDraghi)于9月发布的报告《未来的欧洲竞争力》。
德拉吉的报告更为详尽、开阔和尖锐,更受欧盟及欧洲媒体重视。欧洲主流精英也在很多场合阐述了与此报告类似的观点。德拉吉报告的主要参照国家是美国和中国(尤其是美国),并将欧洲的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与欧洲发展模式联系起来。可以说,该报告代表了欧洲主流精英关于欧洲发展模式特点、其所面临困境、困境的原因及主要解决办法的系统、清晰的阐述。
首先,德拉吉报告概括了欧洲发展模式的特点,对此作高度评价,并称应坚持此模式。报告如是概况欧洲发展模式:“欧洲模式结合了开放的经济、高度的市场竞争、强有力的法律框架以及消除贫困和财富再分配的积极政策。这种模式使欧盟既实现了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和人类发展,又降低了不平等程度。”报告指出,欧洲绝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就牺牲欧洲的基本价值观:“欧洲的基本价值观是在可持续的环境中实现繁荣、公平、自由、和平与民主。欧盟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欧洲人能够始终受益于这些基本权利。如果欧洲不能再为其人民提供这些权利———或者不得不在它们之间进行权衡取舍———那么欧洲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换言之,欧洲主流精英十分重视欧洲发展模式中所蕴含的“公平”和“积极非财富再分配”,并不打算在任何改革中舍弃此特色。报告在列举欧洲所取得的成绩时自豪地指出,“欧洲的收入不平等率比美国和中国低约10个百分点”。报告还特别指出,民众对全球化的反感恰恰说明,欧洲应该比过去更加重视社会融合问题———“只有在强有力的社会契约的配合下,转型才能为所有人带来繁荣”。
其次,报告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指出了欧洲发展模式当前面临的困境。 从内部看,欧洲的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这使得欧洲缺乏实现其社会和地缘目标的底气。“欧盟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壮志,如实现高水平的社会包容、实现碳中和以及提高地缘政治相关性等,这些都有赖于稳健的经济增长率。 然而,过去二十年来,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美国,而中国则在迅速追赶。”据称,欧盟的劳动生产率从1945年相当于美国的22%上升到1995年的95%,但随后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回落到美国水平的80%以下。而从外部看,冷战结束后支撑欧洲经济增长的三个外部条件——贸易、能源和防务——正在逐渐消失。欧盟是非常依赖国际自由贸易的经济体。2000-2019年,欧盟的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从30%上升到43%,而美国则从25%上升到26%。然而,多边贸易秩序目前深陷危机,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能源方面,俄乌冲突后欧盟停止使用俄罗斯油气,失去了廉价的油气资源。在防务方面,欧盟长期依靠的美国“保护伞”和战后长期享有的“和平红利”也消失了。
最后,报告给出了欧盟的应对思路。欧盟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竞争力;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外部环境的“公平”和“和平”。对于面临不公平竞争环境的个别行业,欧盟应该创造必要的公平竞争环境。 这一点,实际上是针对一些国家的“国家补贴”等政策。报告又指出安全是可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因此欧盟还要抵挡重大的地缘政治冲击。这一点主要指的是俄乌冲突对欧洲安全架构造成的损害。
值得指出的是,从德拉吉报告看,一方面,欧洲主流精英认为,欧盟在提高竞争力时,虽然要调动市场竞争,但不想让“市场”不受限制。比如,报告在指出欧盟要在创新方面向美国学习的同时,也强调“应避免美国社会模式的弊端”。而另一方面,欧盟精英认为,欧盟在维护有利国际环境的同时,虽然应该发挥国家和欧盟的作用,但不应该让“国家”压倒“市场”。比如,报告专门指出,提高竞争力“不应被狭隘地视为一场零和游戏”。欧盟不能一心提高全球市场份额、提高贸易顺差、制造产业巨头,因为如果这样做,可能就会扼杀竞争和创新,还可能会压低工人工资。虽然欧洲应该大力发展高新前沿技术,但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培训工人的技能,否则“人工智能也可能破坏欧洲的社会模式”。
简言之,欧洲精英将美国和中国作为自己发展模式的主要比较对象,希望从中得出应对国际秩序动荡的有益启示。某种程度上,欧洲从美国学习了“市场”,从中国学习了“国家”。但是,欧洲珍视自己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希望维持其价值观、追求相对均衡的发展,并不希望变成“美国”,也不希望变成“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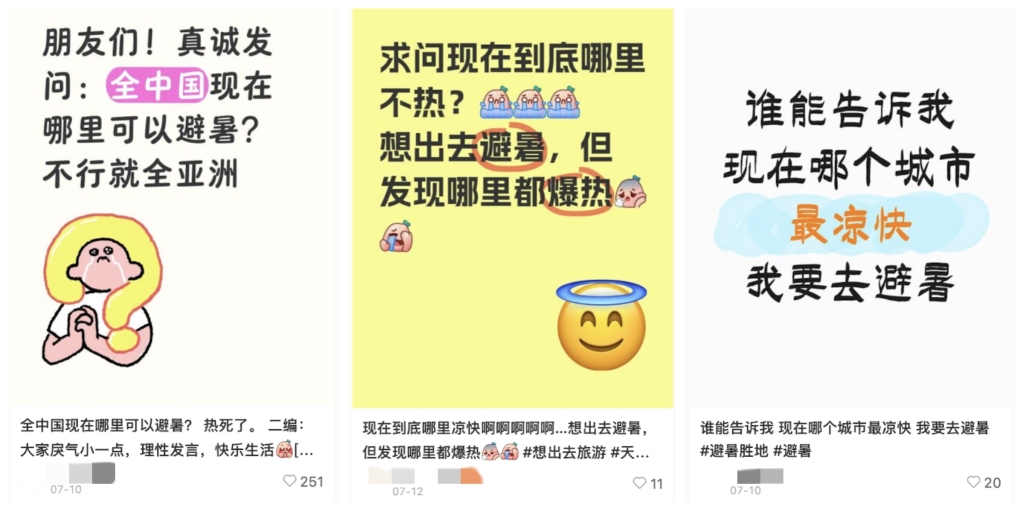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