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图②:电影《东极岛》海报。 图③:电影《戏台》海报。 图④: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海报。 图⑤:电影《长安的荔枝》海报。 以上图片均为出品方提供
二〇二五年电影暑期档——新表达 新空间(艺文观察)
任姗姗
上映13天,《南京照相馆》票房超过17亿元;截至目前,2025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过74亿元……“无论题材类型还是风格样式,今年的暑期档电影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追求,能够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喜好的观众。”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
7个普通人“威武不能屈”的抗战史诗,一个唐朝小吏的千里奔波,一条“取经”路上的寻找与确信,一座“戏台”演绎的悲欢与离合……自6月开启暑期档以来,数十部中外新片接力上映,涵盖了喜剧、悬疑、历史、动画等10余种类型。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南京照相馆》的观众满意度居2025年电影首位。观众评分网站上,《南京照相馆》《罗小黑战记2》《戏台》等影片评分超过8分,开分后又分别迎来涨分。网友评价:“今年绝对是质量过硬的一届暑期档!”
对新表达的不懈追求,是今年暑期档电影的最大共性,也是赢得观众、打开新空间的主要经验。
电影《南京照相馆》的表达,“新”在摆脱了宏大叙事容易“见事不见人”的窠臼,开阔了对主旋律和重大题材的理解。该片集中笔墨“写”普通人在生死关头的大义与坚守,及其背后的精神脉络与人文底色。电影主创以正确的二战史观、严肃的创作态度,传递当代青年对历史真相的探求与思考,唤起全民族共同记忆,有力呼应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大主题。
动画片《浪浪山小妖怪》《聊斋:兰若寺》的表达,“新”在以丰富的想象力“再造”了文化资源。二者分别从经典文学出发,创造性运用当代生活体验和现代价值观进行“故事新编”,抵达观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在“小猪妖”和他的“取经”小伙伴身上,观众看到自己的影子;《聊斋:兰若寺》改编《画皮》故事仅凭一句台词,就彰显对旧家庭观的扬弃……影片所激发的共鸣,都与“我”正在经历的,以及“我”正在关注的有关。
电影《长安的荔枝》的表达,“新”在找到古与今的结合点,拓宽传统题材的主题辐射面。电影《戏台》的表达,“新”在找到戏剧与电影的结合点,延展喜剧电影的表达半径。
“今年或将是国产电影创作的转型之年,艺术把握能力和对社会情绪的敏感度,成为热门影片的两大要素。”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暑期档多部口碑影片“不再单纯追求场面的宏大,而更注重故事的完整;不再单纯追求情节的刺激,而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更重要的是,不再单纯追求类型化的表达,而是寻求与大众情绪、时代精神的深度契合”。
新表达,还包括在电影工业化支撑下的技术突破与视听创新。即将上映的电影《东极岛》,将水下、水面、海上、船体的拍摄与特效技术相结合,水戏团队规模上百人,累计水下拍摄达70天,美术置景团队按照战俘船及同类型船只搭建巨轮四大部分,仅船体侧舷置景就占地2万平方米,能抗12级风的模拟。
新表达,不仅为国产电影开辟新的叙事空间、新的审美空间,也拓展出新的市场空间。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从观众画像看,今年暑期档观众男女比例相比去年更为均衡;从年龄分布看,《酱园弄·悬案》《罗小黑战记2》《恶意》的年轻观众占比突出,《戏台》40岁以上观众的占比超过40%,大幅超出其他影片。
新表达的完成,源于对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返本开新。不论是将镜头对准用生命保护侵华日军罪证的平民,还是用寓言性故事拷问面对诱惑坚守理想的可能,不论运用新的视听语言还是采用传统拍摄手法,暑期档影片反复锤打的是“如何成为更好的‘我’”这一主题,追求的是对世道人心的度量与观照。
2025年,适逢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这一年由横空出世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惊喜开篇,在暑期档沉淀诸多思考。面对新的技术和新的媒介,电影的语境比以往更加纷繁复杂,今天的中国电影人接续百年传统、续写时代新篇,必然要有乘风破浪的魄力与信心,必然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
让历史真相不被掩盖和遗忘
电影《南京照相馆》导演、编剧 申奥
前几天,我们几位电影主创重回南京。与电影里那个断壁残垣的城市相比,眼前的这座城市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88年前,日军曾在这里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敌人曾如此丧尽天良,更不会忘记,那些为抵御外侮不惜献身的先辈们。
我的姥爷参加过新四军,我从小就听他讲述关于正义与和平的故事。12岁,我看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国产电影《屠城血证》,在心底埋下种子。2023年,电影《志愿军》的编剧张珂给我讲了四五个正在孵化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南京照相馆》。
好的创作,把虚构的东西拍得像真的一样;不够好的创作,真实的东西也会被拍得像虚构的。所以,每次创作我都非常依赖文献、纪录片、回忆录、采访等资料。《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为载体,我们搜集了大量出版物、纪录片、相片,曾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搜集素材。
看过那么多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在那一辈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可敬、崇高,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念。而大量有信念的普通人并没有在历史课本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他们的抗争。
这段历史值得一讲再讲,今天再拍,最主要的是与当下产生连接。今天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几乎是实时传播的。而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一张张照片不仅是对暴行的记录,对历史的存证,更是重要的信息传递。剧本策划向我提出一个概念:侵华日军在中国发起的不仅是一场热战,更是一场舆论战、文化战。以往有不少讲述热战的电影,还没有影片特别准确、聚焦地揭露这场战争背后的文化掠夺、舆论争夺。我们决定沿着这个思路尝试。电影中,孙中山先生题字的牌匾被肆意涂抹,井上的办公室摆满抢夺来的古玩字画……这些都揭示了文化侵略的意图。
电影一定有戏剧的部分,要扣人心弦,也要保证绝不能歪曲历史。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十分关键。从建组之初,我们就要求所有人都以高度的使命感和严肃专业的态度面对创作,一定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避免细节上的纰漏。在我看来,电影就是一个时代的影像见证,电影作品也是“活”的历史教科书。通过一部电影,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这是多么崇高的使命,创作者必须慎之又慎。
影片的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我还想表达团结的意义。影片中的人物能把这些罪证传递出来,根本上是因为团结。14年抗战,从被动挨打到赢得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希望这部电影在引发大家的讨论后,形成一种凝聚力。
8月7日开始,《南京照相馆》将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上映,后续还将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观众见面。当年,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一个胶卷、一本底片,让这一历史真相不被掩盖和遗忘。希望这部电影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反法西斯是全人类对于和平的共同期待,和平的成果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任姗姗、刘阳采访整理)
“长期主义”就是“戏比天大”
电影《戏台》导演、主演 陈佩斯
从话剧《戏台》到电影《戏台》,这一路我们走了10年。说实话,10年前刚排这台戏的时候,哪敢想能演这么久啊!每次演出,我们都当作第一次演,都往戏里带点新琢磨,不是一味讨好,更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在剧场里跟观众一点点磨出来的。观众在这个地方没笑,回去就得琢磨;这个地方效果好,想想节奏还能怎么更好。戏要常青,就得像以前的老艺人说的“带活气儿”。既要守住根本,又要懂得让戏“呼吸”。
我做喜剧,刚开始确实是因为热爱。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能把人逗乐特别有成就感。但干着干着就发现,喜剧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它背后连着的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气儿。《史记》里写的“优孟衣冠”是春秋时期的讽谏故事,今天看,那是最早的喜剧表演。现在的喜剧,说到底,是在传承一种活法儿。
好的喜剧,一定是讲对人有用、对社会有意义的故事。但这个意义不是硬塞给观众的,而是藏在那些荒诞的情节里、角色的困境里,等观众自己发现。这才是我心目中喜剧该有的样子。
喜剧的厚度得往文化的根上找。我们这部戏里有很多细节。为什么戏箱不能随便坐?一个戏箱,装着上千年的讲究。拍的时候,光考据这些细节就花了大力气。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喜剧冲突得从文化土壤里长出来。我们要尊重自己所做的这件事、这个舞台。尊重了,有了敬畏心,才能更好地传承。艺术是可以创新,可以突破,但根儿不能丢。就像种树,你修剪枝叶可以,但把根刨了,树就活不成了。
我从2001年回归舞台,心里想过:离开这么多年,观众还记得陈佩斯是谁吗?但只要舞台上灯光亮起来,熟悉感和踏实感就回来了。最怕的不是观众不接受,是怕自己对不起这方舞台。我们站在舞台上,能看清每个观众的表情。观众乐了笑了,心里就有底。这个皱眉了,那个打哈欠了,这戏就得再想想怎么改。舞台就是你给它付出真心,它还你精气神。只要有观众看,我就会一直演,有戏演、有观众等你,就是最大的幸福。
从电影到电视,从电视到舞台,再从舞台回归电影,我尝试过多种艺术形式。像唱戏的行当,生旦净末丑,各有各的味儿。最早拍电影用胶片,成本金贵,不能轻易出错,压力挺大,这种压力逼着自己在镜头前更留神些,把每处细节再磨得细些、稳些。电视这个载体能把你的表演带去千家万户。话剧舞台的反馈是实时的,台下坐着千把观众,你抖个包袱,笑声立马“砸”脸上,很过瘾。这次把《戏台》拍成电影,算是融合了各种艺术形式的特色和优势。话剧的筋骨,舞台的现挂,电影的镜头语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里头得装着真东西。
现在流行说“长期主义”,其实就是老艺人们常挂嘴边的“戏比天大”。您看那些老戏班子,都是一代代人在“死磕”。搞创作就认一个死理儿:戏是磨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也得有这股子轴劲儿,为了一句台词能磨半宿,为了电影里一个不起眼的道具或者台词的气口较真,即使观众不会注意到,我们自己心里得门儿清。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别想糊弄观众。不管潮流怎么变,该守的规矩一寸都不能让。
(刘阳采访整理)
排除杂念,才能奔着最好去!
电影《你行!你上!》导演、编剧、演员、剪接 姜文
《你行!你上!》的故事主人公是郎朗,一位在我们的关注下成长起来的国际知名钢琴艺术家。我们从各种新闻报道里知道了他的事情。且慢,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却往往未必真的熟悉。我想与观众一起体验:你是不是知道,还是有待于知道,或者你以为知道,或许并非真的知道。
如果说有一个计划是100位导演一起拍这个故事,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拍出来的那个不一样,就是导演的印记。创作者带有自己的印记,这很正常,也很必要。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林黛玉,一定带有他的视角、他的印记。所以,我怎么看郎朗,很重要。我停下来,一年两年三年,去观察、去书写、去拍摄。前些年,我得到一个机会陪伴孩子们成长,我发现人和人的关系往往被忽视,尤其是亲情,所以拍了这部电影。
这个故事讲郎朗和他的父亲,更是讲那些敢于梦想、敢于梦想成真的人们。热爱可以让人超越极限。郎朗一天弹12个小时钢琴,并不觉得累和苦。电影里有意思的是,他的爸爸发现他能干这个,有想法,还有办法。有想法特别好,必须得有办法来辅助,想法才能变成现实。这是我在电影里想表达的。
还有一点就是,排除杂念,才能奔着最好去!人往往绊在一些杂念上。其实你能走得更远,不知道哪来的杂念,或者听说了一些潦草的信息,成了绊脚石,让你没有坐下来想一想办法,就直接走了。这也是达不到最终目的和内心向往的原因。
题材并不天然决定电影拍得好不好。《你行!你上!》里,郎朗去德国、日本参加的钢琴比赛,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性赛场,跟奥运比赛类似。现实当中,没有一个钢琴学校会为学生们设置一个水池,我拍的是我脑子里的钢琴学校。这部电影可以想成是动作片、体育片、战争片,甚至比那些的竞技性还强,而且带有美妙的旋律和音乐。
想导好一个戏,剪接好一个戏,事先写好剧本很重要。演员水平的发挥,也得在剧本的基础之上。我相信那句话:没有伟大的演员,只有伟大的角色。与演员合作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故事给到他。
如今网络发达,大家露脸的机会多了,说的话都能被听见了。问题是都这样,也就等于都不这样。你要是不认真,对自己不负责任,还是“零”。就像电影里的这句台词:你得抓住你能改变的事情。为你不能改变的事情而焦虑,没用。改变了自己,还可能改变环境,继而改变更多的人,给更多人带来生活上的便利,那才是更有意思的一生吧。
(任姗姗采访整理)
为观众呈现熟悉的“上美影”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隽
网友说,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是一部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动画片。这部电影延续了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1》中《小妖怪的夏天》的同一世界观,讲述4个无名小妖怪怀揣英雄梦踏上“取经”路的故事。影片以“小人物”的视角、全新的叙事架构和中国动画的视听美学,开启“西游故事新篇”。
“我是看着‘上美影’动画片长大的。”观众的深情表达,既是对“上美影”作品的喜爱,也饱含满满的期待,激励我们用心创作,用更新更美的作品赓续中国动画的美学风范。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60多年以来,创作了500多部(集)美术动画片。从《大闹天宫》民族风格的确立到《浪浪山小妖怪》的全新上映,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浪浪山小妖怪》的创作轨迹,映射中国动画产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既要传承好数十年积累的艺术传统,又要直面当下娱乐方式多样化带来的审美意趣的更新迭代。
“不重复自己,不模仿别人”,是“上美影”一直坚持的创作理念与艺术追求。电影产业自有一套标准化、工业化的流程,而完整体现中国画的笔墨、意蕴,是工业标准无法定义,也难以机器化生产的。对于今天的动画电影制作,如何在艺术个性化和制造工业化标准之间寻求平衡点,是必须直面的挑战。
《浪浪山小妖怪》汇聚监制陈廖宇、导演於水等超过600人的主创制作团队,精细打磨1800多组镜头。在多位前辈艺术家的指导下,20多位画师完成近2000张场景。在视觉表现上,影片采用中国传统水墨动画,又非单纯沿用传统绘画技法,而是融入透视、光影、运镜等现代技法,形成新的镜头语言,力求让观众看到熟悉的“上美影”。
“西游”故事家喻户晓,今天如何激活这个IP,体现当下的时代感、让观众认同,是我们一直思考的。《浪浪山小妖怪》延续了“上美影”作品强寓言性的特点,聚焦《西游记》中无人关注的“平凡小妖”,“补写”了《西游记》故事外的一段空白,用“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组成的“无名取经团”映射我们的现代生活。我们希望用有意义、有趣、令人共情的表达,使新的“取经”故事走进观众内心。
从点映开始,我们就密切关注观众的反馈。“老少皆宜”“呈现国风美学”“开辟西游题材新赛道”……观众的一系列鼓励中,有对电影创作十分重要的启示:扎根生活沃土,只有反映美好情感与生活向往的作品,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向经典和传统要创意,中国神话、传说、古典小说,始终是中国电影、中国动画创作的“富矿”;弘扬“中国动画学派”的传统,弘扬真善美,是我们创作的永恒追求。
将创新思维与当代审美、现代生活相融合,用时代精神激活动画的原创力、创制力、表现力,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活力奔涌。
“笨功夫”是电影人的真诚
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主演 大鹏
创作电影《长安的荔枝》,是我导演生涯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辗转七地取景拍摄,同时在组人员最高峰值是1300人。有时实在挨不住了,我就用一位前辈的话鼓励自己:“做有意义的事情都难。”幸运的是,拍电影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身边有一群前赴后继的伙伴,我们一起扛过来了。
第一次拍摄古装片,为让影片的细节经得起推敲,我几乎是恶补唐史,一口气买了40多本与唐代相关的书籍,不断查阅、对照,还要与服化道、美术、摄影等各部门反复沟通。历史要准确,审美要当下;既不能悬空古意,又不能让观众觉得有隔阂。如何拿捏这种“古今尺度”也是难点。语言方面,用语过古,会让人产生距离感;太现代,又容易出戏。我们努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尽量让观众听得懂又不失年代感。
我经常刷到很多“《长安的荔枝》十大金句”一类的短视频,每次刷到,都会截图、保存,提醒自己在改编的时候要记住,这些是观众喜欢的、读者喜欢的,不要去随意改变它。
电影《长安的荔枝》中,我既是导演、编剧,也出演了主人公李善德,从青涩少年一直演到两鬓斑白的老者。李善德,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基层小吏,咬牙去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被这种“不是英雄却硬着头皮扛事”的劲儿打动了。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也时常觉得自己正经历一场能力边界之外的挑战。他的焦虑、坚持以及硬扛的劲儿,我都感同身受。
电影里,李善德运送荔枝5000里,拍摄中,我们同样一路奔波。技术飞速发展,虚拟拍摄固然可以“一日千里”,但实景的真切没法替代。岭南的湿热、山路的泥泞、演员一身的疲惫,这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有一次,我们在广东阳春拍完,又赶赴罗定。几百人花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现场,造型、走位、航拍一气呵成,拍完又连夜撤离。最终那一组镜头,在成片中不过几秒钟。有人说这是“笨功夫”,我觉得,这应该是电影人的真诚,这种“手工感”会累积出整部电影的气质。
今年是我作为导演的第十个年头。有人问:你总是在塑造“小人物”,这是主动选择,还是创作惯性?我不是这么出发的,却是这么抵达的。可能我之前演了类似的角色让人印象深刻,于是这样的角色会容易找到我,变成了一种创作惯性。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普通,有血有肉,踏实生活,热爱生活,有一些无可奈何,却依然愿意为只有一次的生命全力以赴。
一个像我这样的创作者,没有任何办法在作品中把自己“藏”起来,是否真诚,是否渊博,是否幽默,最后都会在电影中纤毫毕现。而无论讲什么样的故事,底色都是我,一个具体的我——比较草根,有学习心态,愿意进步,肯下苦功夫,有些笨拙,但很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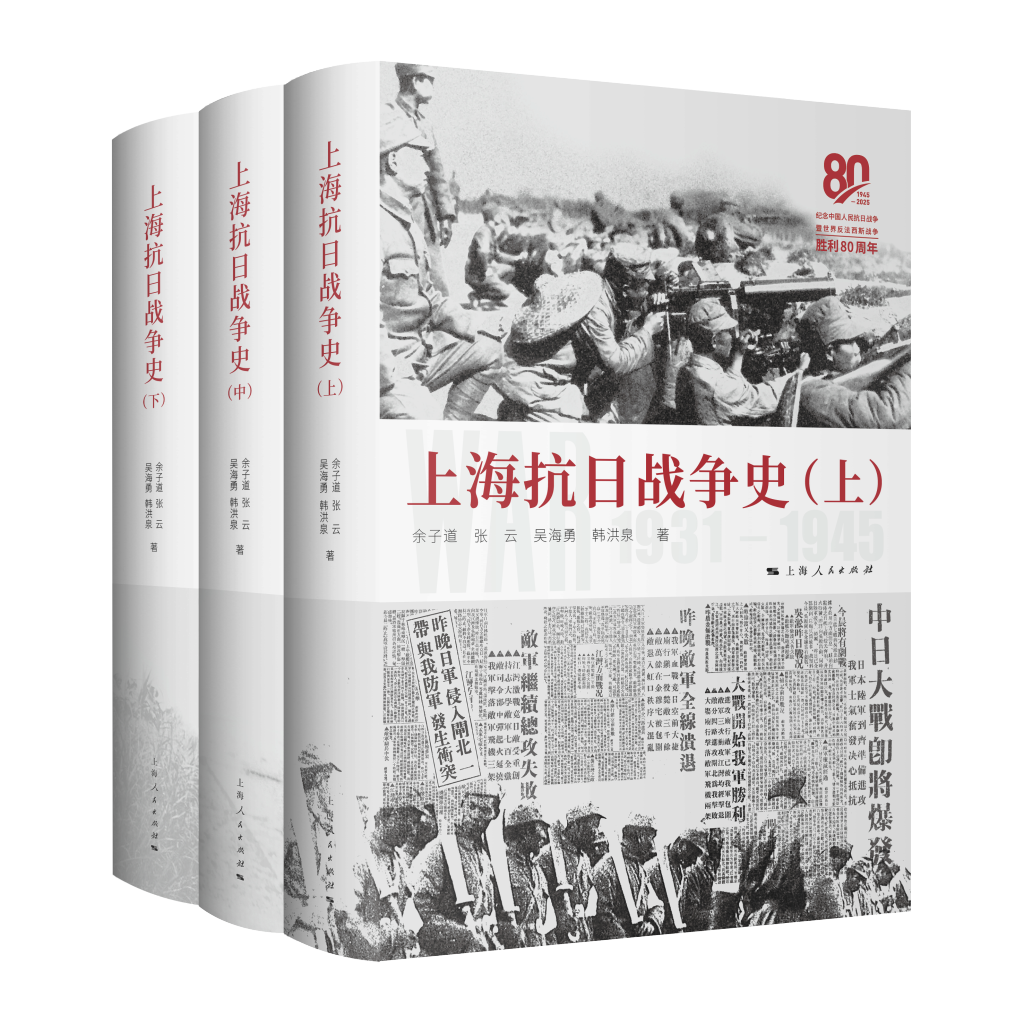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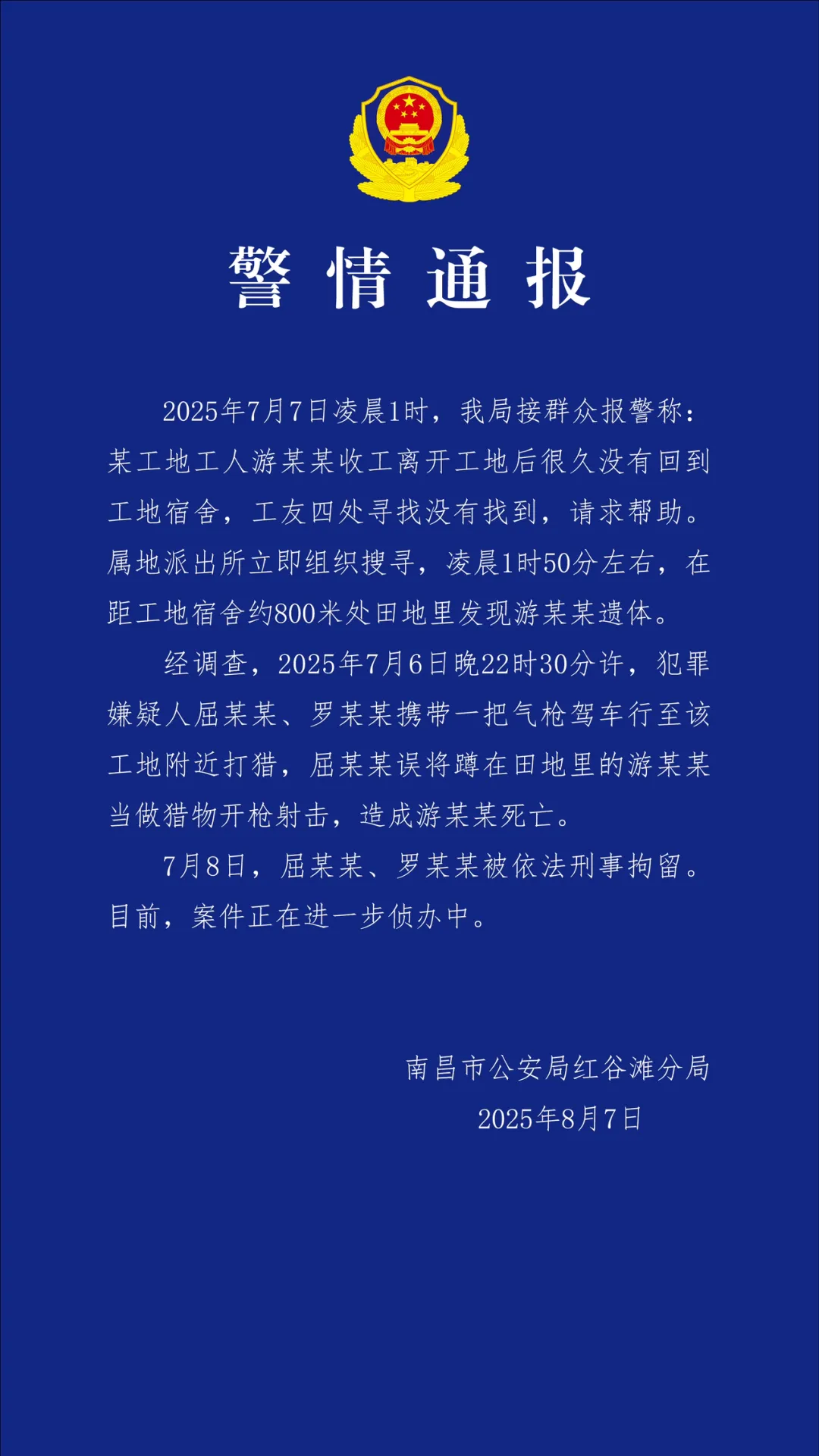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