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专栏“Una voce”,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4年7月到2024年9月间的五则短文。

吉奥乔·阿甘本
犹太教的末日
不理解这点,就没法理解今天以色列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历史上真实的犹太教的双重否定。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就它把基督教的民族-国家转移给犹太人而言——不只代表了从18世纪末开始的那个逐渐抹除犹太认同的同化进程的顶点。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如阿姆农·拉兹-克拉科茨金(Amnon Raz-Krakotzkin)在一项堪称范例的研究中展示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意识的根基,是又一重否定,是对Galut也即对“流亡”这个我们所知的,犹太教所有历史形式的共同原则的否定。早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前,在圣经文献中就已经有对流亡概念的铺垫了。流亡是犹太人在大地上的存在形式本身,而从密释纳到塔木德、从会堂建筑到对圣经事件的回忆,整个犹太传统都是从流亡的视角来构想、体会的。对一名正统犹太人来说,甚至在以色列国生活的犹太人,也处在流亡之中。根据托拉,犹太人等待的那个与弥赛亚一同到来的“国”,和现代民族国家毫无关系——这个“国”的核心,恰恰是重建圣殿和恢复献祭,而这些东西,是以色列国听都不想听的。别忘了,在犹太教看来,流亡不但是犹太人的状况,也和整个世界有缺陷的状况有关。根据包括路力亚(Isaac Luria)在内的一些卡巴拉学者的看法,流亡定义了神的处境本身——神正是通过出离自身的流亡创造世界的,并且这个流亡将持续至Tiqqun即初始秩序的恢复。
正是这种对流亡的毫无保留的接受,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当前一切形式的国家的拒绝,才使得犹太人要比那些向国家妥协的宗教和民族优越。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是唯一(两个)拒绝国家形式、没有发动过战争、没有沾染他人之血的人群。
因此,通过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否定根源上的流亡和流散,犹太复国主义背叛了犹太教的本质。那么,这个背弃造成另一场流亡——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并使以色列国认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最极端、最残酷的形式,也就不奇怪了。对历史——在犹太复国主义看来,流散本来是会把犹太人排除到历史之外的——的顽固要求也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但这可能意味着,也许,在奥斯维辛没有死去的犹太教,在今天认出了自己的末日。
2024年9月30日
科学与幸福
尽管我们相信我们从科学得到了好处(l'utilità),但科学不能让我们幸福,因为人是一种说话的“是”(un essere parlante),需要用话来表达欢乐与疼痛、快感与苦恼,而科学从根本上说以一种沉默的“是”(un essere muto) 为目标。和世界上所有的对象一样,这种沉默之“是”的数量和大小也是可以被认识的。而人说的自然语言至多是知识的障碍,如此,必须对自然语言加以形式化和纠正,把那些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欲望与想法、钟爱与反感时首先注意的冗余当作“诗性的(poetiche)”给消除掉。
正因为面对的是沉默的人,所以科学永远无法产出伦理。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会怀着科学的兴趣,毫无顾忌地在被送进集中营或被关进美国监狱的人的身体上做各种实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事实上,科学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分离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即我们可以在各个层面上,把一个活的“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和它的关系生命(vita di relazione)、把人与植物共有的沉默的植物性生命(vita vegetativa),和他作为一个说话的“是”的精神存在(esistenza spirituale)分开。在今天,记住这点是好的:人似乎已经把他们所相信的一切抛到一边,把对幸福的期待托付给了科学,而这样的期待只会遭遇失望和背叛。正如近年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的那样,用医生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生命的人也因此而愿意放弃他们最基本的政治自由,无限制地服从治理他们的权力。幸福永远和那些我们为交流而来回说的简单的话,和那些欢声笑语,和那些使我们不知道是因为痛苦还是快乐而流泪的感动(commozione)密不可分。让我们把科学家留给数字的沉默与孤独,让我们警醒地看守着不要让他们入侵伦理和政治的领域,那唯一能够真正让我们满足的领域。
2024年9月8日
关于乌克兰的一些知识[1]
在被当作自明的真理重复的谎言中,有一个是这么说的:俄罗斯入侵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它没有以任何方式说明的是,这个所谓的独立国家,是直至1990年起才有的,在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它一直先是俄罗斯帝国(自1764年起,但在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它就被纳入莫斯科大公国了)然后是苏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到底,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俄语作家果戈里可能也是乌克兰人,他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精彩地描述了那个当时被称作“小俄罗斯”的区域的风景和在那里生活的人的习俗。准确地说,还应该补充这么一点,那就是直到一战结束,我们今天称之为乌克兰的领土的很大一部分,还在奥匈帝国最偏远的省级行政区加利西亚名下(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约瑟夫·罗特就出生在一个乌克兰城市,即东加利西亚地区的布罗德)。
重要的是,别忘了,自1990年起我们所谓的乌克兰共和国的边界,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完全一致,并且历史上发生过的,波兰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奥斯曼人对这个区域的持续瓜分也不可能为其边界提供任何事先的依据。因此,虽然看起来矛盾,但乌克兰国家之所以有同一性可言,靠的全是它所取代的那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至于在那片领土上生活的人口,也是一个多样的群体,除十五世纪大规模迁徙到这里的哥萨克人的后裔外,还包括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在大屠杀前,一些城市的人口有一大半都是犹太人)、吉普赛人、罗马尼亚人、胡楚尔人(在1918年到1919年间他们还短暂地成立过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宣告乌克兰独立,在一个俄罗斯人看来,和对一个意大利人来说宣告西西里独立(这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假设,别忘了,1945年菲诺奇亚罗·阿普里勒领导的西西里独立运动就为捍卫该岛的独立而与宪兵队起过冲突,并造成数十人死亡)没多大差别。更不用说如果美国的一个州宣布独立(它属于美国的时间还要比乌克兰属于俄罗斯的时间短很多呢)并与美国结盟会发生什么了。

1991年8月25日,乌克兰人在基辅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前挥舞国旗庆祝乌克兰独立。
至于当前乌克兰共和国的民主合法性,众所周知,其三十年的历史,以多次因舞弊、内战和或多或少隐藏的政变而无效的选举为标志。2016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甚至因此而宣布,乌克兰至少需要花二十五年的时间,才能满足使它能够加入欧盟的合法性要求。
2024年8月2日
[1]注意阿甘本从来没有在或者说只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民族国家的思维框架内思考问题,这篇文章也不是要在与之配套的国际法的框架内争论谁对谁错。他针对的毋宁是那些在关于俄乌问题的讨论中被停留在法律-合法性框架内的西方左翼认为自明的,却未加以细查的实情。
西方安魂曲
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犹太学的奠基人之一莫里茨·斯坦施奈德(Moritz Steinschneider)宣称——这一言论引起了很多持正统观念的人的公愤——可以为犹太教做的唯一一件事情,是确保为它举办一个它所应得的葬礼。可能从那时起,他的判断也适用于教会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化。不过,事实上发生的却是,斯坦施耐德所说应得的葬礼一直没有举行,无论是当时对犹太教来说,还是现在对西方来说都如此。
在天主教教会传统中,葬礼的一个不必可少的部分,是所谓的安魂弥撒。确切来说,安魂弥撒开始时咏祷的导经(Introito)是这样的:Requiem aeternam dona eis, Domine,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主啊,请赐予他们永恒的安息,并让永恒的光照耀他们)。直到1970年,罗马的祈祷书还规定,在举行安魂弥撒的时候,要在继抒咏中加诵《震怒之日》(dies irae)。这个选择与这个事实完全一致,即定义为死者举行的弥撒的那个术语本身(即安魂),就来自一个描述末日的文本,《以斯拉启示录》(l'Apocalisse di Esdra),这个文本既提到了安息,也提到了世界末日:requiem aeternitatis dabit vobis, quoniam in proximo est ille, qui in finem saeculi adveniet,“他将给你永恒的安息,因为在时间尽头来的他是近的”。而在1970年,教会在废除《震怒之日》的同时,也放弃了一切末世学的实例,因此,这一决定完全符合定义现代性的,无限进步的观念。这个被丢掉(人们在抛弃它的同时却没有勇气起来解释为什么)的东西——震怒之日,末日——可以被收集起来,作为在权力终结之时,用来对付权力的懦弱与矛盾的武器。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即,试图不带滑稽模仿意图地,而是在教会(它属于死者的数目)外,为西方举行一场简短的葬礼。
Dies irae, dies illa
solvet saeclum in favilla,
teste David cum Sybilla.
震怒之日,如
大卫和西比拉所见证的,
世界灭为齑粉的那一日。
它是什么日子?肯定是当下,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每一天都是震怒之日,都是末日。今天,世纪、世界正在燃烧,我们的家也在随之而燃烧。我们必定和大卫、和西比尔一样,是这一景象的见证者。那些依然沉默、不做见证的人在现在或以后都将不得安息,因为确切来说,西方不能也不想看到或思考的就是安息。
Quantus tremor est futurus
quando iudex est venturus
cuncta stricte discussurus.
当审判到来,
严格审判一切,
会有多少恐怖。
恐怖不是未来,它是此时此地。而那审判就是被召唤来宣告审判,宣告我们时代的危机(Krisis)的我们。我们必须恢复人们为了给例外状态正名而持续谈论的“危机”这个词的审判原义。在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词汇中,危机指的是医生必须判断病人将死还是将活的那个时刻。同样,我们也要分辨在西方,什么正在死去,什么还活着。审判将是严厉的,不会有任何遗漏。
Tuba mirum spargens sonum
per sepulchra regionum,
coget omnes ante thronum.
Mors stupebit et natura,
cum resurget creatura,
iudicanti responsura.
在全世界坟墓中传播
妙音的号角,
将把所有人召唤到宝座前。
当造物再度起来,
应答审判者,
死亡和自然都会震惊。
我们不能复活死者,但我们至少可以精心准备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审判的奇妙工具,然后让它毫无畏惧地回响,把自然和死亡从用它们来治理我们的权力手中解放出来。在我们身上感受自然和死亡的震惊,在此时此地遇见另一种可能的生活与另一种死亡,是我们唯一感兴趣的那种复活。
Liber scriptus proferetur,
in quo totum continetur,
unde mundus iudicetur.
Iudex ergo cum sedebit,
quidquid latet apparebit,
nil inultum remanebit.
那本包含一切的
书将开启,世界
将经由它被审判。
一旦审判者就位,
隐藏的都会出现,
一切将得到报复。
写下来的书是历史,它总是谎言和不义的历史。真与正义没有历史,它们只会在一切谎言、一切不义的决定性危机中瞬间显现。在那个点上,谎言不再能够覆盖现实。事实上,正义与真在显示假与不义的同时自显。什么也逃不过它们的报复之力——只要恢复这个词在词源上的意思:在罗马审判中,报复者(il vindex)即示力者(che vim dicit),即向审判者展示施加于他的暴力——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报复”——的人。
Quid sum miser tunc dicturus,
quem patronum rogaturus,
cum vix iustus sit securus.
那么,苦命的我该说什么,
又该呼唤谁来为我辩护?
因为正义者很少是安全的。
为审判发声的义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审判并无法呼唤他人来为自己辩护。没人能为证人作证,他只有他的证言——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安全,他处在他的时代的危机之中——但他仍然宣告了他的证言。
Confutatis maledictis,
flammis acribus addictis,
voca me cum benedictis…
Lacrimosa dies illa,
qua resurget ex favilla
iudicandus homo reus
被判罪的人被诅咒,
被扔进活的火焰,
称我为有福的人……
那天是流泪的一天,
当有罪的人从灰烬中起来
被审判。
尽管震怒之日赞歌是为死者求安息与怜悯的弥撒的一部分,但它依然维持了被判罪的人和有福的人之间、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区分。事实上,在末日,施害者——就像现在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事实上正在做的那样——将驳斥自己,任由掩饰自己的不义和谎言的面具掉落,把自己扔进自己点燃的火焰。末日、震怒之日、每一天,对他们来说都是流泪的一天,也许,正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点,所以他们才会如此地强装微笑。只有许多人的共识和恐惧才能持续地悬置那一日。因此,就算我们知道自己在权力面前是无力的,我们也必须更加毫不留情地审判,我们不能把审判和我们正在举办的安魂弥撒分开。主啊,别让他们安息,因为他们不知何为安息。
2024年7月11日
帕西淮的公牛与技术
在帕西淮——她为与公牛交配而让代达罗斯打造了一头(中空的)人造母牛——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的范式。从这个视角来看,技术是这样的手段:人试图通过它来达到或再次达到动物性。可这正是今天,人类——通过技术的过度增长——正在冒的险。人工智能(它看起来是技术达到极致的成果)试图生产一种像动物的本能一样,不受思想的主体干预,自行运作的智能。它就是代达罗斯造的母牛。人的智能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这头母牛快活地与公牛的本能交配,变成或再次变成动物。不奇怪,这样的结合诞生出的,是一头牛首人身的怪物,被锁在迷宫中、以人的血肉为食的米诺陶。
在技术那里——我想说的是这个——重要的实际上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人的发生(antropogenesi),即灵长目人属的“成人”(diventar umano),并非一个在编年时间(corso)中一旦完成便永远完成的事件;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在持续“变成人”的同时,也依然是动物。如果说人性是如此地难以定义的话,那恰恰是因为,它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它接合了两个异质却又密切地缠绕在一起的元素。这两个元素不断的牵连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而所有西方的知识,从哲学到语法、从逻辑到科学以及今天的控制论和信息技术,从一开始都参与了这个牵连。
不应忘记,人性不是某种可以获得、或凭个人意志规范地固定的既定之物:相反,它是一种必须不断地贯彻,每一次贯彻都会被推迟、被更新的历史实践(因为这个实践必须区分又接合人的“内部”和“外部”,“活的”和“说话的”,“属人的”和“属动物的”)中“被给予的东西”。这意味着,人性的关键在于一个本质上属于政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决定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人,就位于“属人的”与“属动物的”、语言与生命、自然与历史之间的这一间隙、这一张力之中。而如果说,一个人像帕西淮那样,忘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家,试图彻底倒向本应同时拉扯他的两端中的一端,那么他只会生出怪物,并和怪物一起陷入没有出路的迷宫。
2024年7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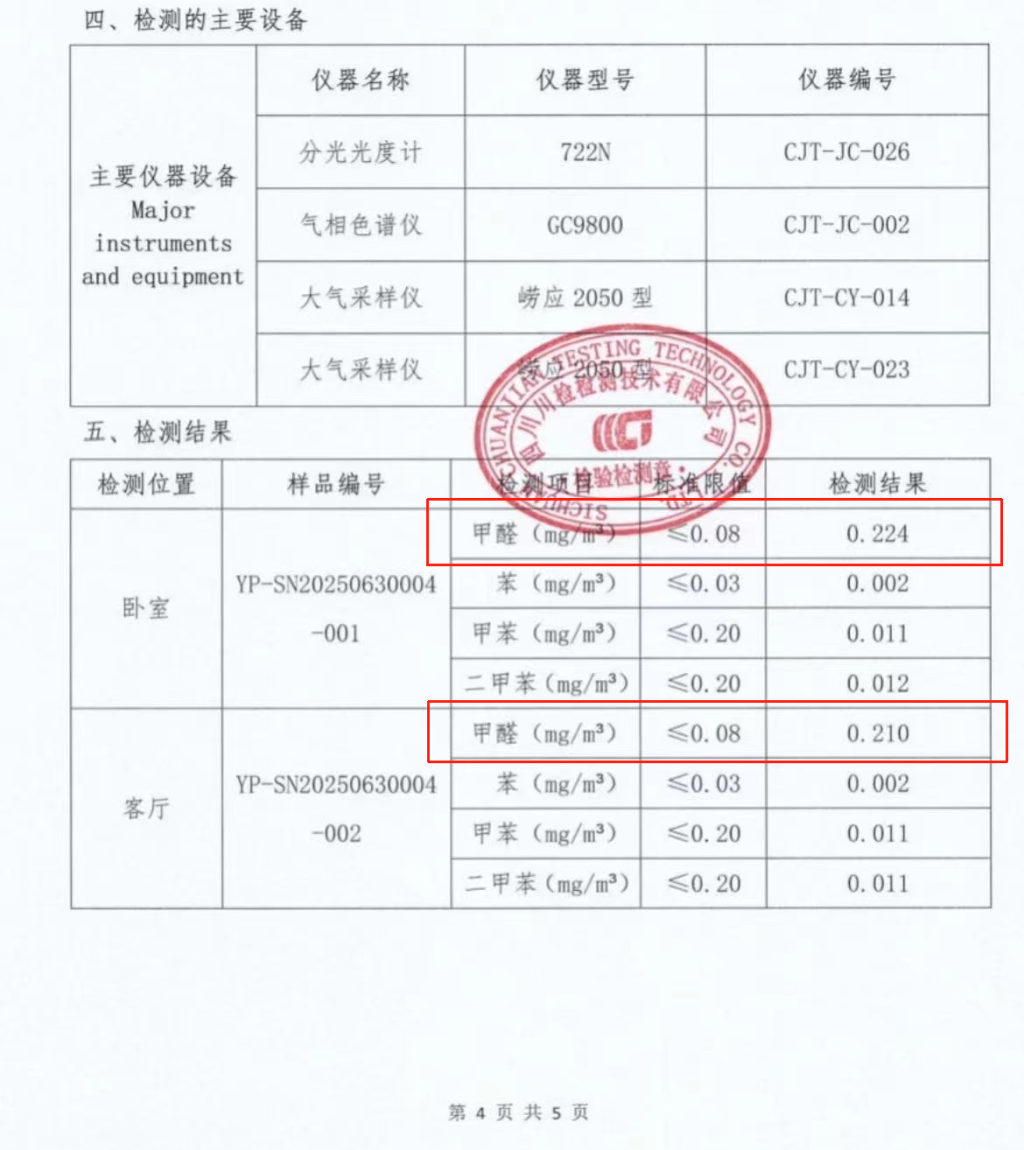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