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提振消费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从数据上看,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6月底,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金刻羽在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新领军者年会上强调,中国能否转型为消费大国将决定中国能否跻身富裕国家。此论一出迅速成为网络上争论的热点话题。
近日,澎湃新闻就消费以及提振消费相关话题专访了金刻羽。
金刻羽表示,当下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鲜明格局,传统大宗消费和基础民生消费增长乏力,以“悦己消费”“文化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力量正蓬勃兴起。
对于提振消费,金刻羽建议,一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比如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二是将财政支持从企业转向家庭;三是投资于能创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物流等;四是改革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以利于工薪家庭;五是加强社会保障托底。
此外,金刻羽还建议,可以考虑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这是扭转“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发展惯性的关键制度创新。
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冰火两重天”格局
澎湃新闻:中国当前在积极提振消费,您如何判断当前中国消费形势,以及近几年来中国消费趋势?
金刻羽:2025年的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鲜明格局。一方面,传统大宗消费和基础民生消费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以“悦己消费”“文化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力量正蓬勃兴起。
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达48.8万亿元,但同比增速仅3.5%,同时,中国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差距显著(2023年中国消费率为55.7%)。
与传统消费疲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消费的爆发式增长,且新消费具备三大特征:轻量化(低单价高频次)、设计化(强美学属性)、文化内涵化(情感价值附加)。
此外,消费市场结构性变化加速显现,呈现多维分化特征。从年龄维度看,银发群体在保健滋补品、白酒、中式糕点领域需求突出,其快消品消费增速远超年轻家庭;从地域维度看,上线城市银发族偏好健康与宠物消费,而下线城市更关注米面等基础品;从消费形态看,服务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商品销售,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提升(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我认为,中国的消费主要空间还是在服务业。商品消费的饱和程度已经不算低,但是服务消费的空间几乎是无限的,尤其在餐饮、旅游、医疗、运动、健康等领域有很大的机会。如果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在80%左右,中国2024年是56.7%,服务业就业比重在发达国家是70%左右,中国不到50%(2023年末,中国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5639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8.1%)。
西方消费市场的成熟形态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美国消费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80%以上,其强大消费力源于三大支柱:信贷体系完善(消费信贷渗透率超90%)、美元霸权红利(低成本获取全球商品)、社会保障托底(医疗、失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这种制度环境使美国居民敢于消费,2024年美国居民消费率达67.8%,显著高于中国。
另外,如果人民币汇率在不久的将来升值的话,实际上也是在增加中国人民的有效收入,可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
打通核心堵点,实现“能花”“敢花”“有地方花”
澎湃新闻:中国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仍然值得关注,您认为影响消费的阻碍因素有哪些?
金刻羽:中国消费率偏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结果,核心堵点可归结为“能花”(收入制约)、“敢花”(保障缺失)、“有地方花”(供给错配)三大维度。
“能花”的障碍在于收入与分配的双重制约。一是收入增长滞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收入分配格局亟待优化。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远高于低收入群体,而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通常达70%以上,高收入群体仅30%左右,这种分配失衡显著抑制了总体消费率。二是资产结构失衡,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不动产占比超7成,这种“房地产化”的资产结构导致财富流动性差,抗风险能力弱。当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家庭净资产大幅缩水,特别是对在2018-2021年高峰期加杠杆购房的家庭,资产减值压力尤为突出。
“敢花”障碍在于保障仍显不足与未来焦虑,导致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医疗、教育、养老等不确定性是很多居民减少消费的首因,这种后顾之忧使居民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高负债也在挤压消费。高负债率直接挤压日常消费,特别是对中产阶层形成“财富幻觉下的消费贫困”现象。
“有地方花”的障碍在于供给错配与场景缺失。带薪休假制度执行率低、文旅设施不足、城市消费空间规划不合理等问题,制约了消费场景拓展。特别是对银发群体、年轻家庭等差异化需求,缺乏针对性场景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整体经济结构偏向生产,而不是偏向消费,整体宏观调控的思路也是重视产业、生产、产能,地方政府很多机会和一些机制也是偏向于供给端、生产端,这些都不利于消费。
发展中经济体总是只注重产能建设、生产和供给,但对总需求的考虑不够充分,这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要更多地关注需求。
澎湃新闻:您认为,提振消费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金刻羽:一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比如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二是将财政支持从企业转向家庭;三是投资于能创造中产阶层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物流等;四是改革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以利于工薪家庭;五是加强社会保障托底。
另外,我还想强调有花钱的情景,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强调全球竞争力,当然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本地经济”上。实际上每个城市有自己的场景,不管是餐饮、咖啡店,还是其他服务等,要形成能到处走来走去、有不同的环境和场景去消费,在周围地区建设更多的能维持下去的消费场景,而不仅仅是比如在某个国家、某个地方的一个节日性消费场景,在日常生活中消费,既能快乐又能给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其他人有了就业机会就又会消费,然后又会给更多人带来就业,循环起来。
澎湃新闻:是不是有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需要改变?
金刻羽:肯定有观念上的东西需要改变。一方面是个体微观角度,要劳逸结合,生活追求的是什么?不是一直工作,而是能够在当下也生活得更快乐轻松一点,当然这是一种结合,我们不能像西方一样不想明天,但是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想明天、只想未来。
另一方面是宏观角度,我们在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设计上,只重视产业、生产力和制造业,实际上远远不够。为什么美国是有钱的大的经济体,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大的消费经济体,其他国家想成为富有的国家,必须得成为一个消费大国。
依赖出口,现在几乎不可能,因为当前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不能光追求谁效率高、竞争力强、能够把所有产品都卖到世界,这种观念现在在国际舆论场上已经很难被接受。我们的宏观管理手段,实际上从需求端入手也是最快的,短期的宏观管理政策一定要在需求端起到很大作用,防止大家信心失落、降低预防性储蓄的习惯。
虽然美国采取了5万亿美元刺激政策,造成后面的通货膨胀,但是也躲过了很重要的经济衰退,它的经济衰退也只持续了两个月时间,肯定是在消费端的刺激非常充足,当然这并不完美,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起码让美国经济很快恢复。
澎湃新闻: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在需求端采取了一些政策,您觉得力度怎么样,还是说可以有一些更激进的刺激政策?
金刻羽:首先,消费者的预期要有改变。一方面,有一些比如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样肯定就想提前消费,而不是对通缩的预期,那样再刺激可能也形成不了持续性的循环。第二,力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第三,肯定还是要更加注重就业,从科技发展角度看,我们非常强调制造业,但是机器和自动化的出现同时在发生,如果过于注重制造业,未来的就业机会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强调服务业就业,因为服务业会提供比制造业更多的就业,当然短期内大家对就业的不确定性还很警惕,所以要从政策端大力度地让消费运转起来,把整个经济的发动机运转起来。
“成为消费大国和富裕国家要同时并行”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要成为消费大国才能成为富裕国家,但有人认为这里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富裕以后才能消费,您如何回应?
金刻羽: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成为消费大国和富裕国家要同时并行,一个是短期的部分宏观调整要靠消费,消费直接变成就业,就业直接变成收入,收入变成更多消费,一个是一个国家长期的潜力,当然在于效率、资本等。但是不能永远考虑的只是长期,短期都过不去,怎么考虑长期?
这个概念是什么?比如,我省了一块钱,就剥夺了其他人一块钱的饭碗,我今天出去消费,就是给其他人就业,其他人就业就是让其他人会去消费,这些消费就变成另外一些人的就业,另外一些人的就业又变成一些其他人的消费。这个不是鸡与蛋的问题。我们早已经过了要先生产、先储蓄的阶段,现在已经不像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只消费不储蓄不投资,我们是投资过多、消费太少,这之间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提高居民收入,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澎湃新闻:制约消费的一个很大因素是收入低,在当前经济承压的背景下,对提高收入,您有哪些建议?
金刻羽:在经济承压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重点突破三个维度。
初次分配改革方面,向劳动者倾斜。一是工资增长机制上,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免税收入门槛。二是财产性收入拓展,多措并举稳住股市,打通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强化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和违规减持;丰富个人投资者债券产品选择。拓宽居民财富增值渠道,改变过度依赖房产的财富结构。
再分配调节方面,强化公平性。一是税费结构调整,降低工薪阶层税负,提高资本利得税比例。2025年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通过转移支付增强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二是社保体系完善,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动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研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减轻家庭负担。三是托育和学前教育补贴。
此外,要重视农民增收,盘活农村资产。一是土地收益分配改革,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探索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户合法住房。这有助于释放农村巨量“沉睡资产”。二是产业兴农,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推进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居民的一大部分财产在房地产里,导致大家不敢消费,您认同吗?如何解决这一部分问题?
金刻羽:居民财富过度集中于房地产是抑制消费的关键因素,这一判断有坚实数据支撑:中国家庭资产中不动产占比高达77%,远高于美国和日本。这种结构导致两大问题:一是财富流动性差,难以转化为消费能力;二是房价下跌引发负财富效应,居民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
有几种解决办法,一是存量去化:允许专项债券支持城市政府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此举既能消化库存,又能补足保障房短板,还可释放改善性需求。二是释放住房需求,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同时申请贷款;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度。三是优化资产结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资产占比。
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澎湃新闻:您建议,可以考虑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具体可以怎么做?
金刻羽:将消费和工资增速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是扭转“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发展惯性的关键制度创新。
其制度效益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导向纠偏,扭转GDP锦标赛导致的过度投资,引导资源投向民生改善和消费环境优化。如日本在1987年转型中将政策重心从出口补贴转向服务消费支持,带来内需持续增长。二是供给质量提升,激励地方政府培育消费新场景。三是资源配置优化,推动土地、资金等要素向消费领域倾斜。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完善城乡消费设施,加强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村终端物流配送设施建设,这正是考核可落地的领域。四是培育区域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引导地方发展特色消费。如成都发展首店经济(2024年引入首店820家),带动消费增长。
考核指标体系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基础指标方面,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服务消费占比、消费便利度指数(15分钟生活圈覆盖率)等。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可成为重要观测项。特色指标方面,可因地制宜设置文旅消费(云南)、银发消费(海南)、数字消费(浙江)等特色指标。环境指标方面,可设置消费者满意度、带薪休假执行率、12315投诉办结率等。《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可作为监督重点。创新指标方面,可关注消费新业态培育(AI消费场景、低空经济等)、国潮品牌孵化数量。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消费指数”纳入地方考核,推动釜山电影节、K-pop产业集群等特色项目崛起,使文化产业成为经济新支柱。中国可借鉴此经验,通过差异化考核激发地方创新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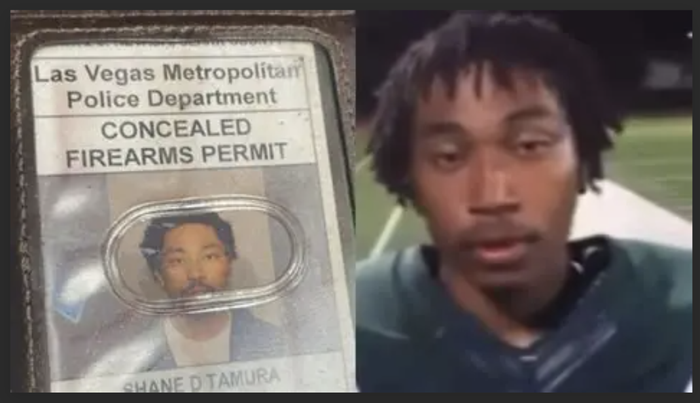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