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于2020年8月6日去世,享年68岁。时隔五年,我们重审斯蒂格勒留下的思想财富,试图理解斯蒂格勒强调的“技术是人学”,思考其观念对于当下社会的影响。

贝尔纳·斯蒂格勒
斯蒂格勒离开我们五年了。临终前的那段时间,他已遭受精神问题的长期折磨,休养了一段时日后,原本以为会好转,但迎来的却是噩耗。斯蒂格勒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他高中便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五月风暴,之后还一度作为劫匪抢劫银行——尽管第二次就失败了。入狱期间他以绝食的方式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单间,随即静思看书,投入了哲学的怀抱。后来,他被德里达赏识,跟随德里达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技术与时间》三卷。当然,他还是一名萨克斯手,担任过蓬皮杜艺术中心音乐方面的负责人。斯蒂格勒与中国学界联系也较为密切,他在南京大学的短期课程被集结出版为《南京课程》,在中国美院的讲座被汇总为《人类纪的艺术》。坊间更是盛传着他如何像传销一般将中国学者拉去国外,在激情演讲中让其为自己的宏伟项目“投钱”。这当然十分离谱,但似乎又格外符合他的人设。
我们今天谈及斯蒂格勒,不仅纪念他的为人与故事。作为一名思想家,更多需要被讨论的是他的思想遗产的价值,以及这份遗产在中国的接受与理论旅行。斯蒂格勒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变得愈发受重视,比起五年前所处的译介阶段,如今不少学者已能够自觉使用其相关思想解决学术问题。尽管相较于几年前的热点效应,如今对他思想的研究已经进入到平缓稳定期,那种各种学术媒体皆谈斯蒂格勒的盛况,在当下已经看不到了。有趣的是,从谈论其人到自觉使用其思想,这一趋势与当下的现实情况也相关。斯蒂格勒去世后,诸如元宇宙、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新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大模型,几乎让整个人类遭受了一次思想与观念上的震撼。文科学界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历史、政治、法律等,对人工智能的讨论霸占了内容输出的相当一部分版面,这种特别的激情,背后既有对新的“学术增长点”的激动,但也有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隐患的担忧。尤其是语言大模型这方面,它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溢出各行业,其带来的如文科无用论与就业难、文学作品抄袭、AI生成图像的法律制约等现象,已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这时,努力试图在社会旋涡中冷静下来的人文学者,在顾及到技术所能引发的忧虑之时,努力证明它所具有的潜力,以及我们能够在这个“技术时代”做出怎样的适应与改变。我们往往美其名曰“与技术共存”。斯蒂格勒的思想于是当然成为其中的宠儿。他的义肢、外在器官、第三持存、负熵等术语,都是介入各类技术现象的便捷抓手。
只是,这种技术深入改变世界的现状,和对技术的广泛讨论,既成就了斯蒂格勒,但也有些颠倒了斯蒂格勒思想的逻辑——斯蒂格勒让我们关注技术、重视技术,将其从思想的边缘带至中心,但他的核心要旨绝非仅仅让我们看到技术以往被忽略的一面,绝非让我们看到在过往、现在与将来中,技术已然成为某种决定性要素让我们与之共生,也绝非让我们在解决未曾遇到的新问题时,能够找到理论支撑与观点依靠。我们于是在这样一种背对潮流的冷眼沉思中,纪念斯蒂格勒,也重审他留下的思想财富。需要强调的是,斯蒂格勒的思想核心始终是“人”,技术是人学,它参与人们思维的运作过程,帮助人类完成自身历史的演进,维持着个体的主体性地位。而完成人学的核心思路,就是“感性认识”。
一、被“选中”的技术
在《人类纪中的艺术》中,斯蒂格勒提出了两次“感性的机械转向”的说法,并将其视为存在于人类命运中的重大危机。第一次机械转向发生在整个20世纪,即本雅明所说的“可技术复制时代”,在这个时期,被资本主义掌控的大工业机构,能够生产如广播、电影、电视剧这样的艺术样态,在不断地批量复制中剥夺了人们,尤其是艺术爱好者(业余爱好者)心中“心理动作知识”(psychomotive knowledge),造成了“感性的无产阶级化”。而第二次转向则发生在近些年,它的形式由模拟(analogue)转为数码(digital),以后者为特征的新技术兴起,使得原本只有大工业能进行生产的艺术样态被下放至个体中。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这导致了业余爱好者的回归,也让处于感性危机中的人类社会看到了一些希望。
概括来说,斯蒂格勒认为发生于技术领域的现象——几乎就是阿多诺笔下的文化工业——造成了个体感性能力的被剥夺,因此也使得个体意识被褫夺。但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人的认识过程,也就是知识的获取其实是依靠感性力量的,艺术鉴赏成为认识过程运作的典型范例,而一旦将感性维度中的含混、神秘等特质转变为确定性的“机械”,我们便迎来了危机。斯蒂格勒强调:“艺术的秘传所涉及的层面,是与其他的一致性平面并存的平面,没有它,任何类型的作品的对象——不论是科学的作品,哲学的作品,文学的作品,法律的作品,政治的作品,还是一般而言的知识的作品——都无法存在。”又是一句玄妙难懂的话,我们努力理解,即知识的获取与艺术的鉴赏是相同的,真正的知识是一种只能依靠主观力量而存在的东西,而那些被转变为那种机械化的确定之物,则根本不是知识。
既如此,斯蒂格勒在这里就区分了两种技术,可以大致称之为“好的技术”与“坏的技术”。在他的思想中,成为人认识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的那种技术,包括20世纪之前的文字、印刷等技术,以及数码时代蕴含的希望的数码技术(的积极一面),可以粗略被我们划归为好的技术,而像文化工业这种技术,则是坏的技术。而两者的关键区别,就是它能否促成个体的感性认识。
那么,为什么往往被冷静、理性、确定性等词语形容的技术,反而要促成人类认知主体的“感性认识”,而作为它的对立面,技术带来的感性的机械化又有何危害?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大致概括斯蒂格勒思想的主要问题域。这一节主要解决前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当然不能贴着斯蒂格勒本人的路线,从《技术与时间1》开头的“技术为何一直在思想史中被轻视”“技术在人类学维度上有何意义”这一视角开始,而是要跳出其外,先来看看斯蒂格勒的思想资源,以及它能够被放置在这些思想星丛中的什么位置。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几乎斯蒂格勒所汲取的哲学思想来源,都与现象学有着关联,其中既有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本人,存在论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也有与现象学关系密切的德里达。即使是看似与现象学无关的,法国技术哲学代表人物西蒙东,也是梅洛-庞蒂的学生,其思想带有着一定的知觉现象学的身影。在一种思想史的脉络中,现象学诞生于观念论的思维方式日趋解体之时。后者极力为知识的来源寻找先验的根据,力求摒除客体“并非为真”的怀疑论倾向。最终,观念论者将世界笼罩于观念之下,主体与客体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性之下产生的,而认识活动则是精神以自我中介的方式不断占有客体,并最终抵达主体与客体绝对同一的理性那里去的漫长历程。所以,认识活动的特点,也就呈现为从自我出发回到自我的反思性结构。熟悉观念论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而这种思维方式实际将所有的知识来源给予了一个大全一体的绝对者之中,因为被它统辖着,我们所有的对世界的认识才拥有了根据,也就排除了那种“眼前的一切并非真”的怀疑论出现的可能性。而作为对这种认识论模式的反对,现象学的重要特征便在于不再讨论这种真或假,以及为了避免出现怀疑论而必然寻找的,使得认识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如果眼前是一棵树,那么它就是一棵树,而不是作为“绝对者为了认识自身而将自身抛至对立面从而让存在者在不断地自我中介与提升运动而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对客体进行占有出现的一个环节”的树。这个立场便是著名的“现象学悬置”。由此,认识活动的关注重点就从为事物之真寻找根据,转移到客体在我们意识中是如何被给予的、呈现的。也就是说,认知主体本身的认识能力。
上面的内容是晦涩抽象的,却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简化的。当主体本身的认识能力被视为重点时,感性与经验的力量也就被凸显了。以往在观念论中被视为最基础但也最低级的认识环节,经验是混乱、不连贯、不统一的,但到了胡塞尔这里,经验本身具有了一种统一性,在我们对事物的感性接触中,一种能够确认正确认识的特质从中涌现出来。我们可以说,个体的认识能力本身有一种先验统一性,它通过经验得以实现,让我们完成正确的认识。不过,这种对主体的认识能力的倚重和探索,从胡塞尔的主体性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继而转至法国时,一个有趣的观念转变是,对认知主体本身能力的信赖感降低了。认识世界并非完全依靠主体的意向意识,这中间也有着非主体力量的参与。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个纯粹发生于主体的意向意识变成了在历史的、被给予的世界理解,也即是现实性的而非超验性的历史积淀,成为了那个先验统一性。梅洛-庞蒂则继续向外一步,身体这个既与精神性的主体紧密关联,但又呈现为精神的对象的“肉”,成为认识世界的窗口。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并非纯粹使用这种先验统一性来认识事物,而是接受那些被给予我们的世界面貌。至于到了新近的哲学学者马里翁身上,这种被动性就变得更为激进化了,几乎是完全将认识活动当作了对世界的被动接受,只是这种被动仍然需要在主体的认识框架中实现,因此在中文学界我们有人会将passive翻译为“受动”来指代这种不可能完全脱离主体能力,但毕竟将客体置于首位的认识过程。如果再往前一步,我们还可以联系到与马里翁同时代的新晋法国现象学学者,以及对现象学进行批判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OOO),但这里就此打住。
这个拐着弯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马里翁的现象学历程,其实是感性维度不断突出的过程。在胡塞尔那里,经验其实并不能称得上是纯感性的,根据康德的概括,感性应当是由外物刺激而产生的混沌的东西(未被图式及概念这类先验统一之物整理),但胡塞尔将这种东西转化为人的意识结构,经验中本身是带有一种先验统一性的,它保证事物在每个人面前的显现都是明确的、一样的,也就是成为知识,而摒除那种混沌的、神秘的私人要素。但是一旦这种对主体认识能力的高扬逐渐被削弱,外部事物在认识过程中有着更大的话语权,那种“因刺激而产生”的感性概念也就得以复归了。感性认识的立场正是在这种视角下得以确立的。而斯蒂格勒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定位,其实介于梅洛-庞蒂与马里翁之间。他对身体的机能并不抱有信心,但也未曾彻底外转,他选择了一个折中的东西,一个和身体一样,与主体紧密相连但又是精神性主体的对象,但是要比身体更加往外一点的东西,来充当认识事物的关键环节。
这也就是技术。
斯蒂格勒拿来了胡塞尔的持存概念,这是他对人主体能力不信任的一大原因。当然,这里也涉及海德格尔的上手、在手等概念,我们为了思路连贯,将其简化掉了。持存概念表示的是记忆,胡塞尔用这个概念概括对外部世界的经验如何保存在脑海中,以便知识确实能够被主体掌握。但是斯蒂格勒认为,纯主观维度的记忆是不靠谱的,因为人会遗忘。对一个事情的经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型、解体,甚至完全消散,而不是永久铭刻进脑海里。斯蒂格勒用了古希腊神话“艾比米修斯的遗忘”来对此做隐喻,大家可以自行搜索这一故事。而这也就证明了,那种通过经验而显现出来的先验统一性,其实是相当脆弱的,至少,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东西将它们保存下来,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提醒我们:原来曾经我们是这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原来对待这个问题的标准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三持存,那个外在与身体的,但是是人为创造、体现人的意志的存在,它比作为肉身的身体更为外转了一些,因此斯蒂格勒叫它“义肢”或者“外在器官”。在斯蒂格勒那里,受到德里达的影响,这种“好的技术”的典型代表是文字,当然他也重点分析过电影。
如此一来,认识活动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活动,即不断揭示被记录在技术物中的那个先验统一性——在《时间与技术1》中,斯蒂格勒用“Méthesis”(获得知识)这个词来指代它,还指出这个词的希腊词根与艾比米修斯的关系,以及海德格尔如何将其视为“一切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根本性先决条件”。毫无必要。但是,正如我们被外物刺激所产生的感性材料是主观的,每一次接触技术物时,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忆起曾经的经验,得到关于事物的一幅图像。因此,我们需要多次与技术物接触,不断和它熟悉起来——比如背古诗,每一次都会比上一次更熟悉,直到几百遍时,我们可以脱口而出。每一次接触,其实就是一次反思,它让我们得到了这个先验统一性的碎片,而将多个碎片拼合在一起,我们大致能够还原出这个先验统一性的面貌。当然,这个过程是主观的,图像的拼合更像是本雅明笔下的“星丛”,在这些感性材料的汇聚中,我们以主观的方式,获得了客观的知识。因此我们说,获取知识是感性认识,而仅靠我们主体本身的能力是无法做到的,技术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个过程,补足了认识活动中缺失的那部分。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重申文初提出的观点了,技术被得以重视并非它“本就应该被重视”,而是在一种思想的理路中,它恰好能够充当一个关键角色,帮助我们完成认识过程。因此,技术并非先天重要却一直在受人忽视的角落阴暗爬行,实际是它是被“选中”升咖的。而技术的参与又势必会让感性因素在认识活动中占据更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它让知识成为一种感性认识。
二、为逻辑寻找历史证据
目前为止得到的只是逻辑上的建构。如同黑格尔体系中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一样,斯蒂格勒也要为这种逻辑上的推演寻找现实中的依据。不过要强调的是,斯蒂格勒的思路其实与本文的行文思路相反——这不难理解,由于斯蒂格勒的写作以一种排他性的视角进行自己的理论构筑,也就是实际强调自己对、别人不对,因此,他要先在现实中寻找案例与材料支撑,尤其是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历史细节打破既有认识,继而用自己新的理论将其囊括在内;而我们的行文是一种借鉴性的视角,即看清斯蒂格勒在诸理论中的位置,以及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未曾关注的东西,自然会先介绍它的逻辑,继而描述它对现实的叙事性征用。
斯蒂格勒对现实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点。其一是他在人类学意义上对历史的解释,即技术深度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其二则显得更有意思,他要证明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由经验自主演进的过程,而非受到某种先验力量的制约(比如黑格尔或马克思那里的历史螺旋上升的过程),而使得这种历史阐释得以成立的关键要素则是技术。前一点不难理解,就是技术史。技术与经济、政治、社会等要素深度绑定在一起,新的发明与革新也昭示着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两者呈现深度绑定的姿态,或者说叫耦合。而技术毕竟没有自主革新的能力,它是依赖于吸引人类对其改进的“技术趋势”来进行革新的,这也涉及人与技术共同面对的历史前进动力。这一动力就是被称为第二热力学定律的“熵增”,简单来说就是目前已知宇宙中,如果不对一个事物注入能量,那么它必然走向混沌和毁灭。比如雪糕放在常温下必然会化掉,想让它维持形态就要使用冰箱(消耗电能)。人类为了对抗熵增,就要用“负熵”来对抗它,而技术成为了负熵的绝佳代言。技术史并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后一点。
如果人的认识是一种感性认识,那么为人类知识提供依据先验之物便理应不复存在。既如此,知识的产生过程、结果都应该是人类自主的决断和选择,对应在现实层面,也就是作为全部经验的总和一般的人类历史,也应当不是有一种必然趋势的。斯蒂格勒在这里引入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也即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后一环节产生差异后,在对前一环节的阐释中得到所谓的“发展规律”,从而并不存在一个本质性的必然趋势,因此人类历史呈现文字化的特征——来自德里达的《论文字学》。那么,有什么显著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呢?答案是,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即从能人开始,历经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到现代人,人类的大脑皮层的纹理逐渐形成并固定,而这些大脑皮层的纹理,(斯蒂格勒认为)与石器时代的工具纹理呈现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大脑纹理是技术工具的投影。因此,人类历史呈现出鲜明的反身性发展过程,即人通过制造技术工具为经验保留下印记,而这些经验又通过外部的技术工具来使得自己得以进化。人与技术共同组成了历史演进的闭环,而这一切都是经验的——大脑皮层逐渐形成的纹理,就像延异的链条一样,后来者对前者进行回溯性阐释,没有先验因素的参与。由此感性认识的逻辑得以在现实层面反映。
其实在撰写这一段过程中,我多次流露出一些不信任的姿态。甚至我需要反复思考,才能勉强关联起延异、大脑皮层、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如果吹毛求疵,斯蒂格勒的逻辑显然是漏洞百出的,但作为一名哲学家而非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他的主要任务并非进行严谨的历史考证,而是完成理论的构建。而作为普通读者,我们主要感受的是他为感性认识这一结论所作出的多方面努力,以完成自己的逻辑确证性。这一部分集中出现在《技术与时间1》的前两章,我们可以称之为斯蒂格勒的“历史哲学”,在这之后便罕见有关于这类论证的文字了。
三、转向“坏的技术”
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1》的结尾写下这样一段话:“‘光时’是实时中的延异的时代,是存在的历史特有的延迟时间的出离,它似乎给延异构成一道屏障,或者对一切差异都构成了一种威胁——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谈论历史的终结和时代的变迁。这种‘光时’如今对度量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也就是对‘特别文化’的要求。这就必然强制性地带来了一种新的记忆策略,它只能是一种技术的思想(无思想的思想,无记忆的思想),它把一切确正的形式所承载的反思性置于眼前,不论这种‘反思性’是多么不可公度(因是非主观的),它所做的无非就是反思起源的原始缺陷。由此在时间的墙上烙下这样一句奇特的论断:无未来。”这段话暴露出一种沮丧与隐忧。尽管在三卷《技术与时间》中,斯蒂格勒对现代技术的整体态度是积极的,也必须是积极的——毕竟这三卷的主要内容是审视并构筑技术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但他仍然多次表示出对当下状况的不信任。我们引用的这句话可以算是这种不信任底层逻辑的一次高度浓缩。而在千禧年之后,斯蒂格勒的著作更多便是关于这种“坏的技术”了,尽管看起来五花八门:青少年教育、政治经济学、精神分析、生命如何值得过、爱、业余爱好者,等等。我们下面便借助这句摘选话,解释一下背后的逻辑。
毫无疑问,斯蒂格勒对当下技术尤其是资本主义钳制下的技术应用,担忧之处在于速度问题。我们在近几年的诸多理论译介和讨论中,都习惯将速度或加速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大基本特征,并为之赋予一种技术革新之下才出现的特定现象。这里常被提及的理论家包括罗萨、维利里奥,甚至韩炳哲。但是,斯蒂格勒告诉我们的是,速度或加速问题并非一个现代技术社会特有的问题,或者说,技术社会其实只是使得速度隐患背后的逻辑条件更容易实现。这一逻辑条件,如上面摘录中说到的,就是破坏了反思性的认识结构——它让那些本来依赖感性的、“不可公度”的反思过程,如今变得显白了。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技术充当了一种外在的“先验统一性”,它让我们完成了认识活动从自身出发,经过了技术这一中介又返回自身的过程,这使得认识过程具有反思性的特征,也使得其成为一种感性认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必须以时间性为基础才是可能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来自德里达的“延异”,但实际上斯蒂格勒秉承了一种相当悠久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至德国浪漫派时期。荷尔德林就曾将“经验”(Erfahrung)放置在认识论的维度。所谓经验,它不同于体验,是外在于主体的、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的东西,获得经验意味着出离主体、走向他者。诗言说的就是经验。欣赏诗歌,就是将自己出离自身,将自己的回忆不断与诗歌中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由是诗歌具有了一种带来真理的功能。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反思性认识框架。在斯蒂格勒这里,诗这种带有神秘性的艺术形式转变成为技术物,经验这种含混的、需要额外解释的东西也被我们用“先验统一性”代替了,但其中的原理不曾变化,形成感性认识需要一个时间流,需要记忆中的图像在技术物的作用下多次拼合在一起,直到成为稳定的、知识性的内容。而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同一个技术物进行多次使用,才足以让这一切得以发生。而在当下,大众文化这样的技术性产品,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和接受,但又不会让人多次使用同一个产品——几乎没有人会将一部短剧翻来覆去看好几遍,几乎没有人会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观看同一条不到十秒钟的抖音短视频。斯蒂格勒从来不认为大众文化产品不具有和严肃艺术相等的认识论功效,但他的担忧是,第一次的使用成为了唯一,而它也就代表了唯一的知识来源,有着确切的形式。这让感性认识的形成过程阻塞,通向了坏的道路。这才有了《技术与时间1》结尾的那段话:坏的技术对反思性的剥夺。让人类面对无未来的窘况。
因此,斯蒂格勒关注的诸多看似与技术不相关的内容,将其与这一逻辑相关联,便变得息息相关了。关注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教育,是因为认识的感性特质使得它只能被“示范”,而不能直接被传递,因此青少年教育成为让认识反思性过程通畅的必争之地。关注生命的价值、爱等元素,是因为它们仍然代表了感性能力的最后一块阵地,与不断加速的社会及感性认识的堵塞顽强斗争。关注业余爱好者,因为他们能够在不断加速的社会中仍然以一种纯然热爱的姿态介入艺术中,从而让认识过程仍然保持一种反思性的向度,不至于变为被动地接受。看似不是技术,但其实处处是技术。
我们不妨进行合理联想,面对今天的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变革,斯蒂格勒的态度会如何?我想,他并不会担心人工智能写作、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等合理性问题,甚至可能对它们津津乐道。这是因为,当我们输入指令时,人工智能最后得出的结果一定不与预想中一致,甚至会误差很大。而这就会被迫开启反思活动,让我们记忆中的图像与新的内容进行对应,从而不断巩固或者更新已有的知识。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创作行为并不会剥夺人类主体的主体性,相反是使主体性高扬的途径。斯蒂格勒可能害怕的是,我们对ChatGPT、DeepSeek等直接进行询问的行为。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对问题作出的解答,仍然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无论正确或错误与否,如果直接依赖人工智能反馈的答案并将其作为知识,那么就使得反思性认识活动的通路堵塞了,最终使人无法形成对某一领域的感性认识。
至此收束全文。本文其实仅仅提供了一个极简版本的斯蒂格勒入门,将他的扛鼎之作,三卷《技术与时间》与后期其他文本做了逻辑上的串联,并且省略了大量细节性的内容。但是,在他去世五年后,我想这种基础维度的再强调仍然是有价值的——斯蒂格勒作为一名技术哲学家,尽管一直声称要为技术正名,其实是在为人的感性能力正名,技术帮助人们完成了感性认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从未做出过诸如后人类、人机协同等论断,他从未将技术的重心放置于技术对人类的改变,而是始终围绕着人,作为拥有感性能力的人本身,去展开讨论。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是人学。在我们不断希望围绕技术来做出新的讨论成果时,忽略这一点,可能导致我们的方向迷失,也可能偏离人文学科特有的气质与本性。
那么,在文章最后,我们还是将视线从思想转移至思想家本身。斯蒂格勒一生充满传奇意味,从激进青年到锒铛入狱,转而走上学术道路,这几乎是当下之人无法复刻的道路。尽管他的牢狱生涯在晚年依旧对他造成困扰,我曾看到报道,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期间,他的监狱记录对他开展在美国的某个项目有着不利影响。这种别样人生经历,以及其不可复制性,也似乎恰恰以肉身实感诉说着的思想核心所在——将一切赋予以感性的,独异的,自主的。而他的死亡,也似乎像一场盛大的献祭,在新技术到来的黎明喧哗中已然呼唤着黄昏的省思,在对诸多新事物的好奇中保持人的坚守,在技术时代变革所带来的诸多不安与躁动之中,增加一份镇定与冷静。我们想念他,我们纪念他。
【7月6日初稿于哥廷根,7月23—24日改于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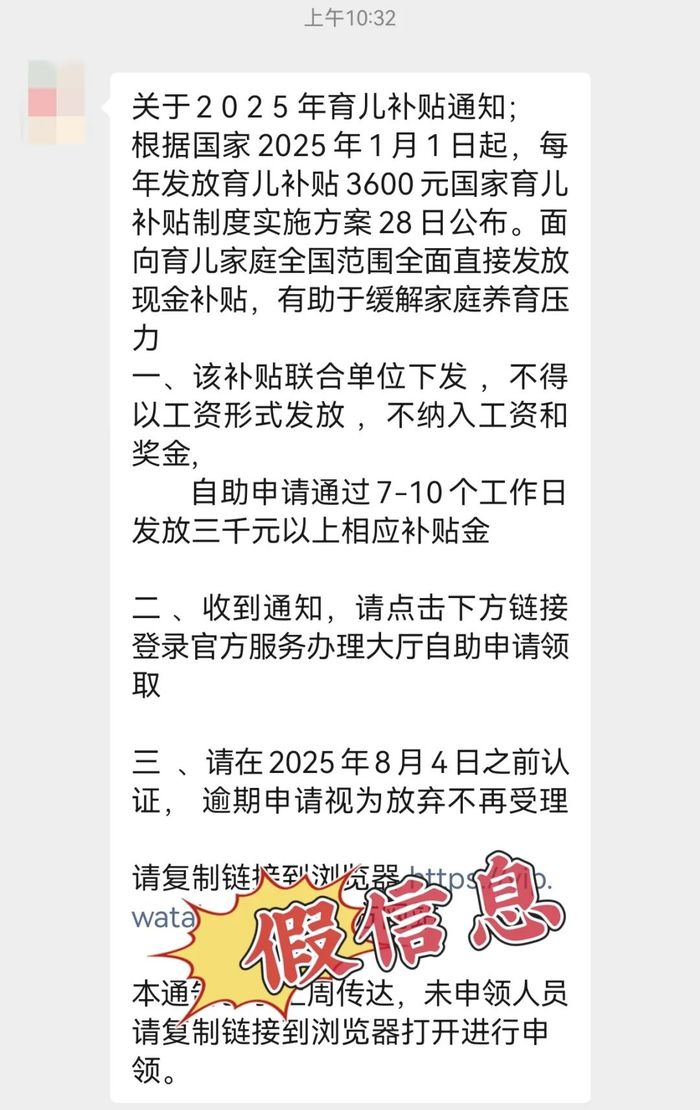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