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是当下英国学术成果最丰厚的俄国史研究者之一,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国际关系史系主任,也是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院士、荣誉研究员和英国学术院院士,目前共出版专著7部,研究方向主要涉及俄罗斯帝国形态、俄罗斯贵族与上层政治、一战和拿破仑战争等。

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
在大众视野中,多米尼克·利芬最为著名的作品莫过于《鏖战欧罗巴》(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Battle for Europe, 1807 to 1814,此书在出版当年获得了拿破仑基金会奖,随后获得沃尔夫森历史奖)以及《走向火焰》(Towards the Flame: Empire, War and the End of Tsarist Russia,出版次年获得普希金故居图书奖),这两部作品都已推出中文译本。今年6月,利芬的最新作品《君临天下:世界历史上的皇帝》(In the Shadow of the Gods: The Emperor in World History)也出版了中译本。但平心而论,这三本书在学术层面的贡献更多在于其对过往思潮和理论的回应,而无法体现利芬对俄国史研究做出的典型贡献,也无法展现英国的俄国史研究在近几十年来面对的理论冲击和自发转向。
200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起编撰的《剑桥俄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三卷本付梓,其中第二卷《俄罗斯帝国,1689-1917》由利芬主编,他在前言中明言希望对该书的编辑施加一些“保守的特质”。他在第二卷中贡献的两章内容既是他过往研究成果的浓缩,也是曾经英国的俄国史研究中颇为“时髦”的范式。近期,三卷本《剑桥俄国史》中译本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读者在留意利芬及其他英国的代表性俄国史研究者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如果能将其与俄国史学在近年的发展趋势及其随后的研究相联系,或许会对当下多国的史学研究趣味有更深的理解。利芬近40年来的学术路径即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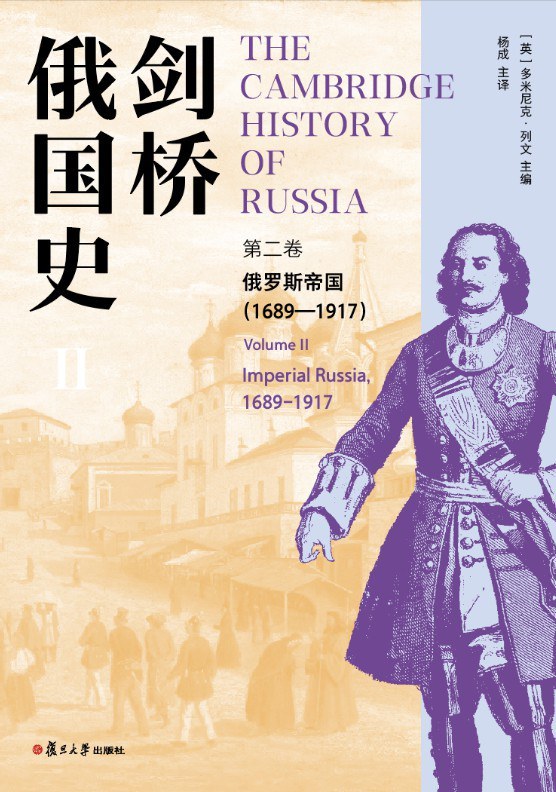
《剑桥俄国史》第二卷
从“一战”到“贵族”:利芬早期的学术路径
利芬的第一部专著《俄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83)充分体现着他所处时代的研究特点:对传统政治史的有限反抗、俄国官方档案的匮乏和作为首部作品的内容上的寡淡。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导师休·赛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的影响。赛顿-沃森是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之前,对民族主义理论构建最成功的学者,其学术核心观点涉及东南欧复杂的民族状况和民族主义思潮。利芬延续其对俄国边缘民族的关注,并延伸出自己的视角,讨论帝俄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手段。他认为,俄国面临的复杂地缘政治局势导致俄国高层被分化为多个不相融的群体,沙皇则因无法平衡各方诉求,不得已让国家投入一场有损自身核心利益的战争。
随后,利芬的学术兴趣转向俄国及欧洲的贵族群体和贵族制度,相关成果体现在他上世纪出版的两本书中——《旧制度下的俄国统治者》(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 1989)和《欧洲的贵族制度,1815-1914》(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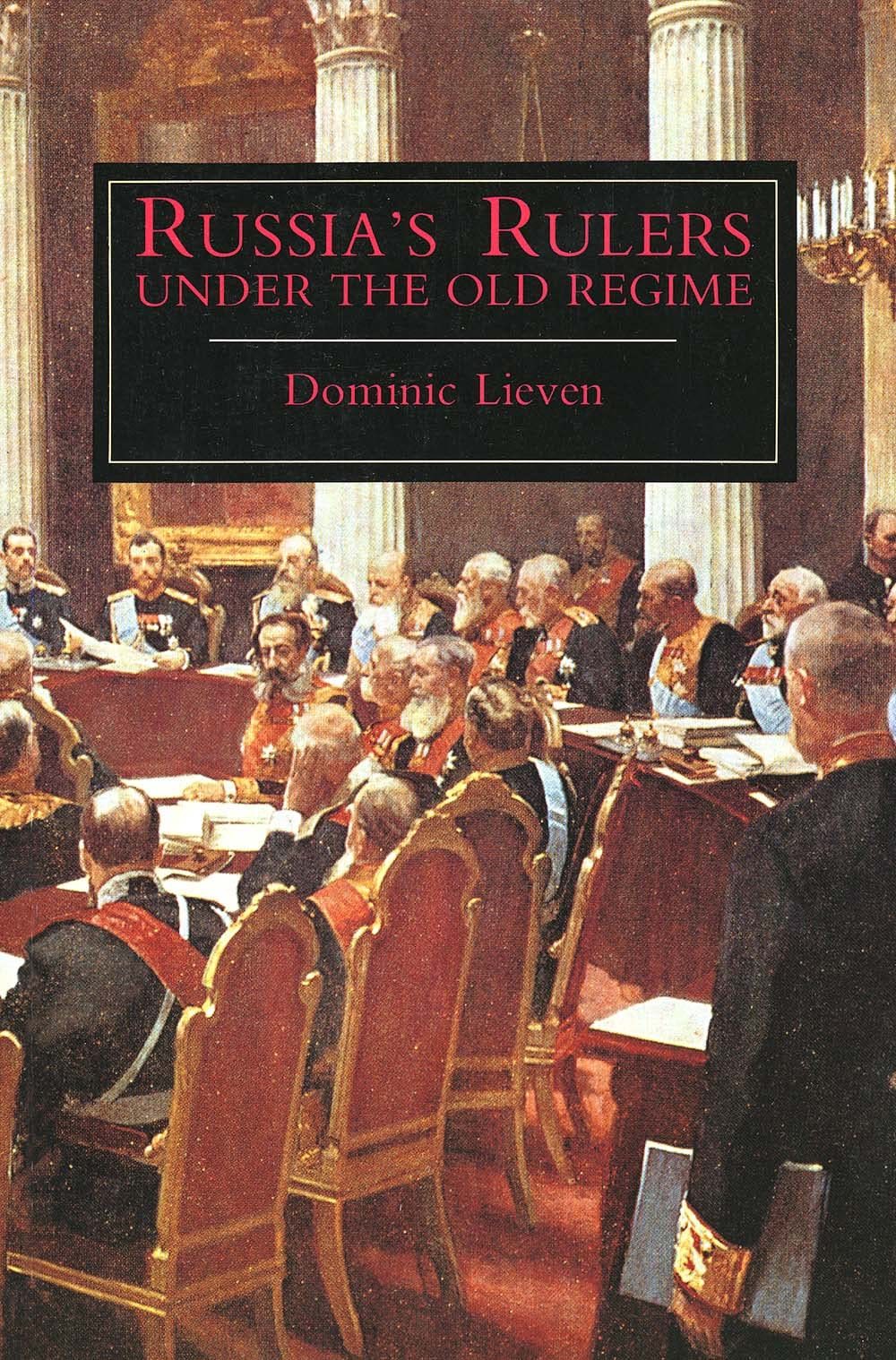
《旧制度下的俄国统治者》( 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
《旧制度下的俄国统治者》聚焦于俄罗斯帝国末期、尼古拉二世在位期间俄国上层统治者的精神面貌。他研究了“国家委员会”这一概念模糊、实际上囊括了215名俄国贵族和社会名流的群体,他们的社会背景、民族构成、教育经历与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在研究思路上,利芬延续了第一部作品对俄国决策群体的关切,并明显继承了罗伯特·克鲁梅(Robert Crummey)对阿列克谢一世和彼得一世时期的贵族杜马成员的研究方法,即通过特定机构筛选出一个不够全面但相当典型的团体,将其视作多数个人而非一个集体,通过写作“集体传记”来展现指挥这一群体行动和决策的复杂精神面貌,而非将其简单地描绘为腐朽阶层或守旧者。在利芬笔下,沙俄的旧贵族家族始终面临个体取向和结构性身份的矛盾,就连尼古拉二世也不例外。俄国的统治精英依据社会地位、民族和部门可以被划分为众多群体,他们既共享贵族身份的社会网络和自保途径,又在政治角力中针锋相对,这些群体远比“官僚精英”这一泛泛而谈的刻板印象复杂得多。利芬的研究实际批判了“突发性”历史解读,将对个体的思考嵌入历史性的权力结构中。
需提及的是,利芬的贵族研究志趣既有学术考量,也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一点从其姓氏“利芬”便可见端倪:在大北方战争中,彼得一世击败瑞典国王腓特烈一世,于1721年签订《尼斯塔特条约》(Treaty of Nystad),瑞典在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土均被割予俄国,古老的利芬家族便随着利沃尼亚的主权转让一同归于俄国的统治下。然利芬家族强烈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色彩始终未被抹灭,并因其不同于俄国贵族的制度传统和文化水平受到俄国统治者的重视。对中国读者而言,其家族最出名的人物可能有1812-1834年任俄国驻伦敦大使的克里斯托弗·利芬(Christoph von Lieven,实际上他的妻子及继任者多萝西娅·利芬[Dorothea Lieven]可能在那个时代更为闻名),以及亚历山大二世的宫廷司仪保罗·利芬(Paul Ivan Lieven)。保罗的下一代转居德国,后移居英国,多米尼克·利芬即是保罗·利芬的曾孙之一。可以说,利芬的家族历史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并成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个人优势。
波罗的海贵族的家族史,以及辗转欧洲各国的经历,使利芬更具比较研究的视野。利芬的研究主题遵循了一条由政治分析逐渐向国家结构性差异过渡的途径:在对俄国的统治精英进行解读后,下一步自然是将这一方法扩展到其他国家,以此完整这一分析系统。于是形成了他的第三本专著——《欧洲的贵族制度,1815-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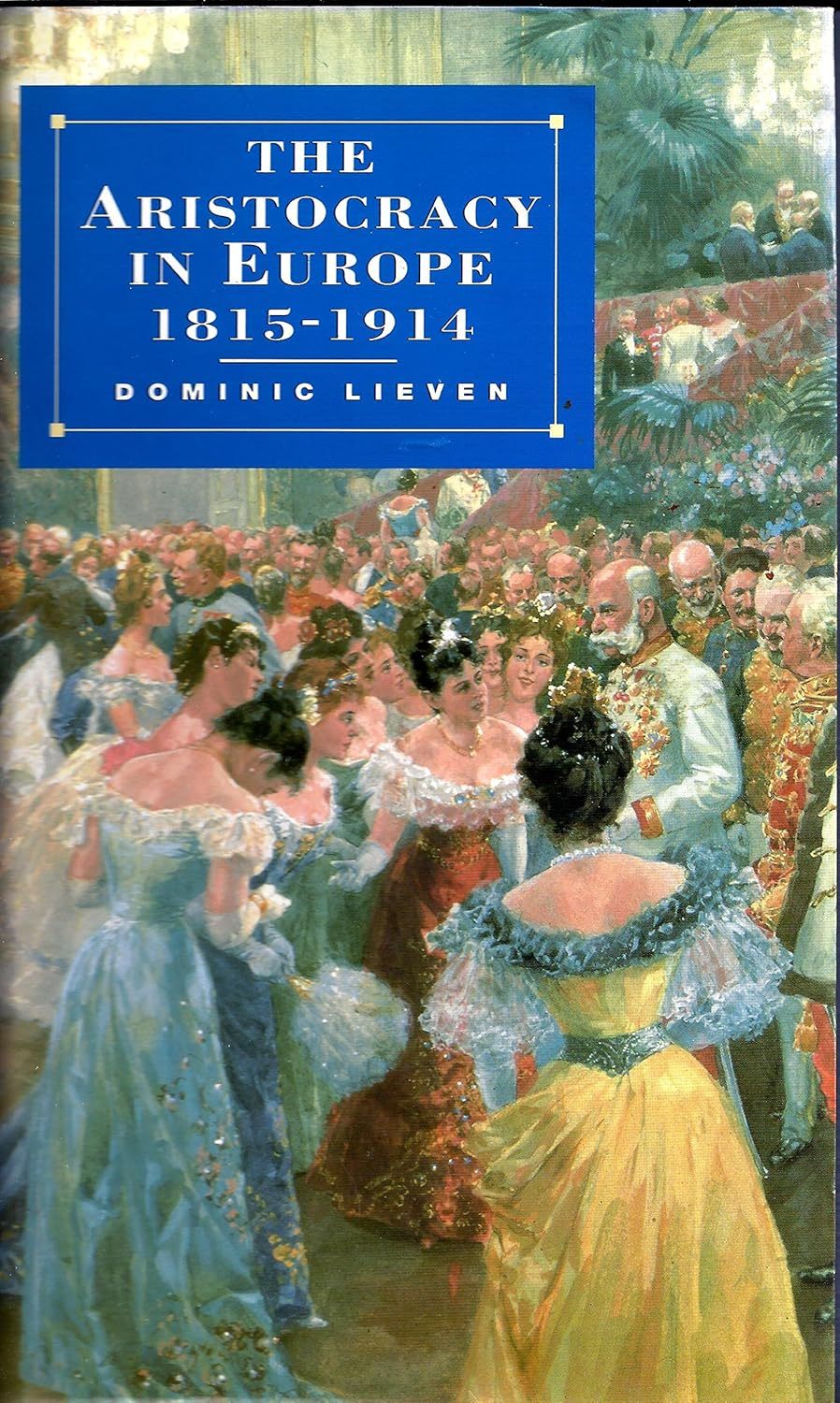
《欧洲的贵族制度,1815-1914》( 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
上世纪末的英国学术圈对贵族史这一常青树领域已略显疲倦,这不单是因为贵族群体的普遍衰微,还因为英国贵族已很好地融入近现代公民社会和资产阶级政治体系,留存下的档案文献数量庞大而详尽,故英国贵族史的研究留存的空白相对稀少,其作为历史分析的主体缺乏学术吸引力,时至近代就更是如此。所以,英国贵族史学家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会抱怨,相较于对现代英国国力衰落的关注,对同样呈现衰落趋势的贵族群体的严肃研究“寥寥无几”。《欧洲的贵族制度,1815-1914》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贵族史学在当代的意义,利芬从他所重视的“传记写作”逐步走向结构性分析和对比分析。书中,利芬遵循对俄国贵族的分析方法,但将视野拓宽到整个欧洲,准确地说,主要是俄、德、英这三个他认为“比其他任何国家更能决定19世纪末和20世纪欧洲的命运”的国家;且鉴于“贵族”一词过分模糊的所指和各国在这一概念上截然不同的历史现实,他将本书的讨论对象框定为客观上具备可观影响力的贵族(magnates)和省级乡绅——这概念适用于英俄两国,就德国而言则是容克贵族(普鲁士)和高贵族(high nobility/Standesherren,奥地利)。利芬的目的在于为贵族制度辩护,不过针对的并非其合法性而是灵活性:他直接反对的是马克思的论断——新兴资产阶级终将“取代”贵族阶层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在他的研究中,欧洲贵族在面对近现代社会转型冲击时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通过与资产阶级和现代政治机器融合(英国)、靠拢专制权力机构(俄国)、扩充土地和军事力量(普鲁士)等方式,贵族群体维护住了他们在19世纪的政治地位,他们亦是现代社会的建设者和政治改革的倡导者,而非单纯遭受现代化的冲击。
纵观以上三本著作,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利芬的研究尽管跨度较大,但基本遵循某类共同主题及其变体,并有一定构建分析范式的倾向。在当时,这种倾向正在成为各国历史研究的主流方向,并反过来刺激同时代研究者做出更大的改变。
帝国范式:利芬的理论成就和“新帝国史”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范式”(paradigm)一词做了现代定义,即能在任何特定时期界定一门科学学科的一套概念和实践。对上世纪下半叶在与社会科学深度融合并实践的历史学而言,范式的使用是一个必然且不可回避的话题,在俄国史领域亦如是。
但若不甚严谨地说,出于历史原因,帝俄时代及之后的俄罗斯史学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特定方向进行历史解释了。这一现象按照托马斯·桑德斯(Thomas Sanders)的说法,源自俄国历史写作中“成熟”和“疏离”的交织:自卡拉姆津后的早期俄国史学家在追求欧洲标准的同时,大多脱离社会其他阶层,甚至逐渐疏离国家现实本身;更贴近下层社会、为其发声的历史撰述者则成为沙皇审查制度和学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长期以来,俄国的历史研究都作为某种远离现实的意识形态或理论的代言而存在。这在18世纪表现为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王朝叙事”的实用主义历史叙事;在19世纪则表现为强烈的实证主义与国家主义倾向——焦虑于俄罗斯民族内部上下文化联通的失败和在欧洲边缘身份认同的危机,俄国学者带着宗教化的期许去审视正兴起的历史科学概念,推崇“无人格化的历史力量与趋势”,使俄国史学忽视了具体事实的论证和时代性事件的记述,转而信仰历史决定论。这一特质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将沙皇内政外交合理化的理论抓手,即将沙皇置于国家与历史指引者的位置,将一切决策视作帝国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苏联成立后,同样的历史分析传统与唯物史观的单向历史发展论一拍即合,互相强化,苏联经典史学就此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大部分时间,俄罗斯帝国史在苏联都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由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树立的对帝俄的批判否定模式被总体上继承下来,其基于唯物进步史观、阶级斗争史观和反沙文主义的分析因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屹立不倒,帝俄的崩溃被简单的历史进步和正义论解读所固化。
将视角转向国外,帝俄史研究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境遇:以俄国史重镇美国为例,受冷战影响而兴起的极权主义范式一度统一了俄国史研究的话语。在这一范式下,苏联因东西意识形态对峙和专制现实而被定性为极权国家,同时由于学界对“东方专制主义”理念的继承,所谓极权文明的特性也被延伸到对俄罗斯民族的定性中,成为他们区别于西方民族的固有品质。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即是这一范式的代表作品。
欧美俄国史研究的另一大范式是现代化范式,它在上世纪50年代去斯大林化的背景下,逐渐取代了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极权范式,将对俄国历史的理解纳入到欧美线性演进历史观的共同轨道上来,强调以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和挫败来理解近现代俄国历史的动荡局面。然这一范式存在着一些固有弊端:其一是进步史观对国家历史进程的解释固化趋向,如帝俄在近代的崩溃,理所当然地被归因于现代化努力的失败;其二是潜在的西方中心论话语,即欧美的现代化道路代表了唯一的文明演化方向,是衡量其他国家发展状况的标尺。这一范式在上世纪下半叶受到来自后殖民理论、全球史观和比较史观的广泛批评,其固化的结构分析法逐渐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现代化”取向。时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现象的现代化改革的彻底失败剧烈冲击了旧有理论,俄国史领域亟需重新寻找新的历史解释方法,于是“帝国范式”应运而生。
利芬是英国学界最早尝试构建这一理论体系的学者之一,或者说他的研究正是“帝国范式”得以形成的养分。2000年,利芬的第五本专著《俄罗斯帝国及其敌人》(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出版,他在前言自述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弥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分野”,换言之是要同时批判当代政治学的实证主义倾向和历史学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重新构建理解帝国政治的历史框架。从学术史角度观之,本书是利芬的集大成之作——它延续了早期著作的主题,为理解帝俄群体观念和制度传统提供了新的更大的架构;它继承了利芬进行比较史研究的尝试,并将范围进一步扩大至亚洲国家(清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更重要的是,由于时代原因,本书得以以更丰富的原始档案文献弥补了早期研究的不足(1993年,利芬的第四部作品《尼古拉二世》就率先使用了新公布的档案,但它在学术层面相对黯淡)。该书聚焦于民族主义和国际强权政治研究,目的是进一步理解俄国历史上面对的帝国困境(dilemmas of empire),同时将其置于全球帝国体系中加以比较,破除“俄罗斯例外论”,重建帝国作为一种普遍政治形态的历史解释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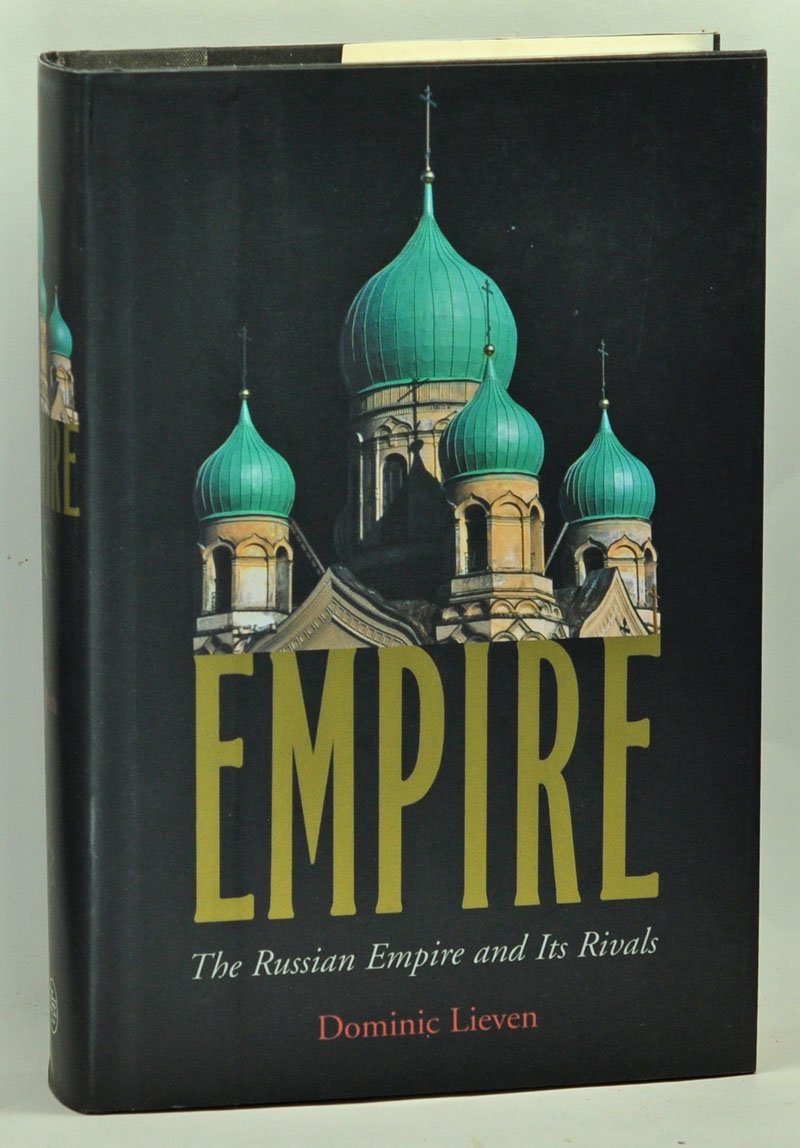
《俄罗斯帝国及其敌人》(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利芬认为,俄罗斯始终未摆脱“欧洲边缘的帝国”身份:第一,俄罗斯是一个标准的帝国,其幅员辽阔,统治人口众多而复杂,以非民主政体和军事力量作为帝国治理的主要手段,并塑造了以帝国为核心的广阔文化圈和政治格局——帝俄与苏联均符合这一定义。第二,地处欧洲边缘的现实赋予了俄罗斯帝国某些特质:因远离欧洲核心的力量制衡,俄国更易通过东扩增强国力;身处欧洲国力第二梯队的地缘性经济劣势,迫使俄国选择直接管控而非间接管理其国域,这宣示了俄国选择独裁集权政体的必然;既靠近又远离欧洲的现实,使俄国人既将欧洲视作借鉴对象,又视作对手,这导致了俄罗斯在国家道路选择和身份认同探索中的徘徊情绪。这构成了分析俄罗斯帝国境况的基本框架。
以近代民族主义为例,利芬的分析正是通过解释帝国本质在民族主义背景下的盈亏,阐明了帝俄统治危机的理论逻辑:自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民族主义和主权在民思想直接冲击了传统帝国,并成为帝国反对者批判帝国政体的理论支点,“多民族帝国”概念首当其冲。对俄罗斯帝国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直接质疑了帝国中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合法性,帝国内的一百多个民族成为国家分裂的潜在力量,随之受到质疑的则是沙皇的统治合法性。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逐渐壮大也对俄罗斯帝国构成了结构性挑战:相较单一民族国家,松散的帝国必须维持庞大的疆域和多民族人口以应对挑战,但这势必激化民族矛盾并加速帝国解体;俄罗斯的相对落后必然使它在对抗西欧的同时引入现代化制度,但这终将强化俄罗斯境内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对沙皇统治形成反噬。旧帝国模式无法应对民族主义挑战,于是在现代国际竞争中节节败退。
这一分析范式即是利芬创设的“帝国范式”。在目前的历史背景下,该范式讨论的主要是帝国政体和民族主义、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该范式适用于19世纪至今的部分政治现实,即它成功实现了利芬弥合政治学和历史学分野的理想。利芬随后也将这一范式应用于对苏联解体的分析,因为他认为苏联实际继承了沙俄作为帝国的绝大部分要素,那么俄罗斯面对的民族主义和西欧意识形态的双重危机就仍然没有改变,随着苏联意识形态的乐观主义和战争胜利的光辉逐渐暗淡,其解体就是必然了。
“帝国范式”引发了各国帝俄史研究学者对帝国特殊发展模式的关注。利芬作为先驱者之一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理论也有着一切早期理论固有的不成熟。由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确立的“民族国家是帝国之后的‘正常’历史发展阶段”的思路早先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利芬的部分理论根基正源于此。但随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概念所根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开始遭到质疑,以它为基准的对俄罗斯历史的批判招致了大量不满,利芬之后的学者大多在继承构建帝国特殊性这一倾向的同时,尝试提出对民族主义困境的新理解或者为“多民族帝国”概念辩护。这一浪潮率先在欧美学界产生,随后被俄罗斯学界接受,并被概括为“帝国转向”(Имперский поворот),其支持者认为帝国具有特殊性质,不能简单地用民族国家的标准加以衡量,于是这种否定民族主义与帝国根本对立的历史书写被进一步称作“新帝国史”(новую имперскую историю)。
一般而言,“新帝国史”以证明多民族政体的合理性为其概念基底,强调大陆帝国相较海洋国家的某种特殊性,纠正民族国家理论对帝国统治特质的一元解释,点明其包容性和多元性,尤其对帝国长期维持其治理稳定的机制作出积极评价。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具体的历史案例研究,避免过度的实证主义倾向。仅欧美学界在这领域就已做出了丰富成果,如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A. Reynolds)在其著作《破碎的帝国》(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2011)中,以俄奥两国在民族问题上的竞争细节反驳了以利芬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不可抗力论”支持者。雷诺兹认为民族政策和对应的民族主义兴起依然属于国家博弈的一部分,是某种政治工具,作为疏离或团结地区人口的手段,其起源于国家煽动而非自主意识——所以民族主义根本不可能是一个脱离帝国语境的替代方案;罗纳德·桑尼(Ronald Grigor Suny)则认为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更多是形式上的,而非治理逻辑上的本质区别。一个例子就是二战后由政府强制力塑造出的所谓“波兰民族”(他称之为“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小帝国”),这否定了民族国家取代帝国的“自然过程”的合理性;必须提及的还有阿尔弗雷德·里伯(Alfred Rieber)所著《争夺欧亚边疆》(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14),该书同样运用了广泛的比较研究法,并将帝国史纳入全球史的分析范畴,视欧亚大陆的历史为一场“对边疆的争夺”。同时,里伯更偏向地缘文化解释,他认为在这些“争议中的地缘政治空间”中,民族边界是模糊、渗透性强且流动的,因此旧帝国与各民族群体之间存在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互动网络。
相关研究在此不再赘述。总体而言,“帝国范式”在对俄国史解释体系的探索中依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见,并为之后的“新帝国史”贡献了部分理论基础,故将其视为利芬的学术高峰并不为过。但就如利芬是“新帝国史”中最“旧”的那一派,利芬本人的保守倾向也逐渐随着学术的前进而逐渐显现。
回望和深化:利芬近年的“保守”倾向
苏联解体一度燃起了英国对俄国史的新兴趣,一方面是由于曾经难以接触的档案全面开放,另一方面源自人们对俄罗斯国力发展前景的正面期待——这是国家实力影响历史研究状况的一个现实例子——英国大学中的俄语学位申请人数达到了历史顶峰。但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叶利钦改革计划的停滞不前掐灭了俄国史研究者对其事业的现实价值的期许,政府资金快速减少,英国大学中的俄国史研究进入一个短期的萧条阶段,这一趋势对俄罗斯相关社科研究打击尤为严重,一个直接的案例就是伦敦政经学院在2001年取消了本科俄罗斯研究课程。
对其时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的利芬而言,这个现实并不愉快。但对比利芬一直“耿耿于怀”的理性选择学派(Rational Choice School)对帝俄史的统御,学科活力的衰减充其量是时代阵痛罢了。的确,“帝国范式”也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但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现实需求和作为学术工作者的职业身份,以及其时学术圈的萎靡状况,利芬选择将当代政治学的一般路数发扬光大,无可厚非。
在努力构建范式之外,利芬自贵族研究的阶段就乐于进行了大量的传记写作——意即排除分析、忠实记录个人化和突发性现象的写作——这一行为受到其师赛顿-沃森的支持,也扎根于他对家族历史的认同。利芬家族自崛起就徘徊于俄罗斯、德意志和拉脱维亚政权之间,他的曾外祖父、外祖父两代则因在印度殖民地服役而将他们家族与另一个庞大帝国联系起来。利芬的家族史本身就是一个帝国全球竞争的缩影,它暗示了范式化的历史理解之下存在众多非理性要素和自主精神,它们无论好坏都被某种整齐划一的话语掩盖,这就是为何利芬一度为19世纪贵族群体的适应力辩护,或者指明帝俄末期统治群体的多样性,或者强调尼古拉二世作为男人和父亲的形象——它们都因不符合大众的历史想象而被忽视,结果是让人们更加远离真实的历史。
2006年《剑桥俄国史》三卷本出版,利芬在由他主编的第二卷前言中直言希望此书在总体上呈现得更加保守,原因是他认为当代英美学术成果“倾向于关注小范围的流行话题。近几十年里,诸如外交政策或俄国经济、金融、财政和军事体系历史等传统话题在英文世界的史学家中变得很不流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章节内容的编排上,第二卷相较其他两卷更加传统,政治制度史、军事扩张史、重大事件和人物史等在其中占据了主要篇幅。利芬本人则贡献了其中的两章内容,基本是他《俄罗斯帝国及其敌人》和《欧洲的贵族制度,1815-1914》二书观点的浓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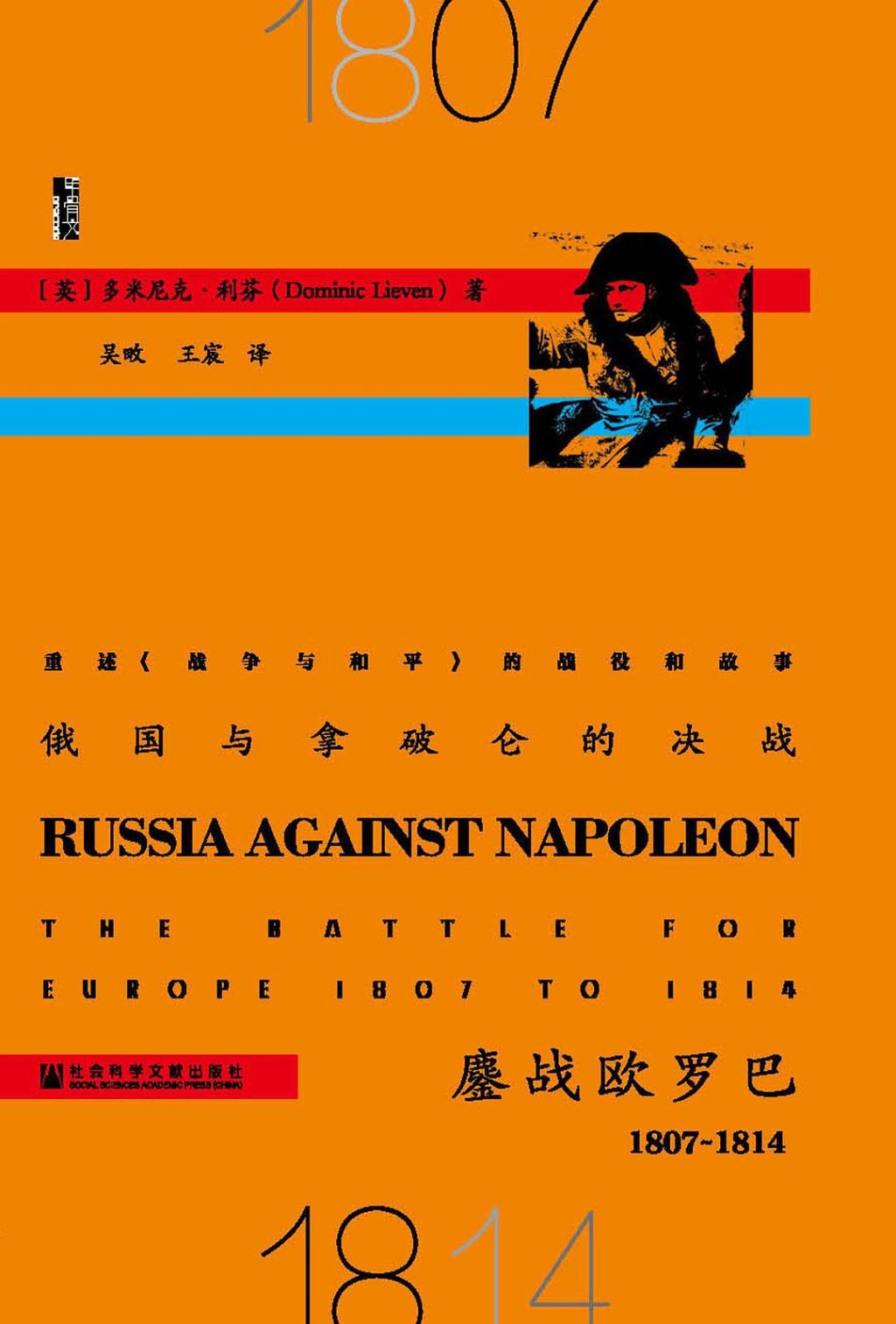
《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 1807-1814》中译本
如果说《剑桥俄国史》前言只是体现了利芬在通史结构上的守旧取向,那么《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 1807-1814》则是他希望在继承自己史学结论的基础上进行保守乃至修正研究的一次全面尝试,这里的“保守”既指它的主题和观点,也指它的研究方法。但实际上,正是在2006年,利芬见刊于《俄罗斯和欧亚史探索》(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上的文章《俄国与拿破仑战争(1812-14)》(Russia and the Defeat of Napoleon[1812-14])就已经提前阐明了《鏖战欧罗巴》一书在史学上的动机及其核心观点:本文/书通过挑战由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塑造的民族主义神话,复原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之下的俄罗斯帝国的实貌,认可帝国的政治和战争智慧,严格辨析帝国面对的国际挑战。这个观点部分继承了威廉·富勒(William C. Fuller)在《俄国的战略和力量》(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1992)一书中对俄军体系和沙皇体制的肯定,以及对拿破仑战争中的民族主义叙事的质疑。利芬认为,在1812-1814年对抗拿破仑的正面战场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帝俄军事力量被赋予了不恰当的历史评价——它在内受到斯拉夫民族主义神话的错误归因和苏联史学的轻视,在外则被各国民族主义叙事选择性忽视。利芬在书中部分继承了早期的分析倾向,如对贵族群体成分的详细分析、对俄奥特殊关系和东南欧状况的强调和对俄国身处欧洲边缘的特殊地缘利益的界定等,但整体上本书属于“理论铺路,叙事为主”,它以大篇幅和时间顺序拆分俄法战争中的每场大型战役、具体政治交涉和高层决策,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对具体战场细节的考察:俄军在交通、内勤、战场纪律、战争财政和指挥系统等各层面都具备显著优势,甚至胜于法国,所以在俄军制定错误战略和反法盟军内部协调混乱的背景下,俄军依然能够带领反法盟军顺利攻入巴黎,彻底结束欧洲动乱。利芬对传统战争史的接纳和发扬,有力论证了“沙皇军队的‘旧政权’性质不仅不是弱点,反而是优势”这一观点,他大胆批驳了“帝国范式”在理解俄国地缘利益方面的不足,转而肯定了亚历山大一世对俄国-欧洲安全的时代性认识。从这个角度看,《鏖战欧罗巴》一书在主题上和之前作品的巨大差异背后依然有一条平稳的逻辑线,并且对利芬个人的学术思考有巨大的价值。
有趣的是,利芬在书中特地提及了其家族分支的一个重要节点人物——夏洛特·冯·利芬(Charlotte von Lieven),时任皇太后玛丽亚的侍女长。利芬通过分析夏洛特的庄园农奴在战争期间的征召入伍情况,指出当时的农奴募兵制度存在人性化和高效率的一面,这背后是村庄社会、富裕农奴和远方领主之间的复杂博弈。这一案例是对关于农奴制的某些单向批判的批判,体现了利芬对单一史观的反思。所以虽然他在前言中戏谑“如果想让一所英国大学把你拒之门外,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说你希望研究的是战争、外交和君王们的历史”,但我们可以看到,利芬学术上的保守倾向蕴含着“改革”思维,他希望挑战的,正是那时还被视为新学术方法的东西,并且事实证明他的挑战行之有效。
不过,悲观地说,相比上世纪几部作品的连贯性,《鏖战欧罗巴》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更多是另辟蹊径而非延续性变革,上文所谈的内部创新只涉及要素而非结构。利芬关于帝国模式的基本主张在此后基本不再变动,其后的作品也都是对这一范式的具体运用和推广。这就是为何将利芬在本世纪的研究称之为“保守”——需强调,这单指理论方法的停滞,绝不意味着利芬随后的研究失去了价值。
2015年,利芬参与主编系利芬集《战争、文化和社会 1750-1850》(War, Culture and Society, 1750-1850)中的《俄罗斯和拿破仑战争》(Russia and the Napoleonic Wars)一卷,在其中发表文章《拿破仑时代的国际关系:长时段视角》(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apoleonic Era: The Long View),延续了欧洲大国战争是“帝国竞争”的界定,呼吁用帝国扩张模型去取代简单的“革命-反革命”解释。文中,利芬认为符合旧制度传统的竞争模式依然高于意识形态对立,各国对欧陆乃至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布局仅是受到革命战争的冲击,其目的、竞争对象并未根本改变,拿破仑战争总体上延续性大于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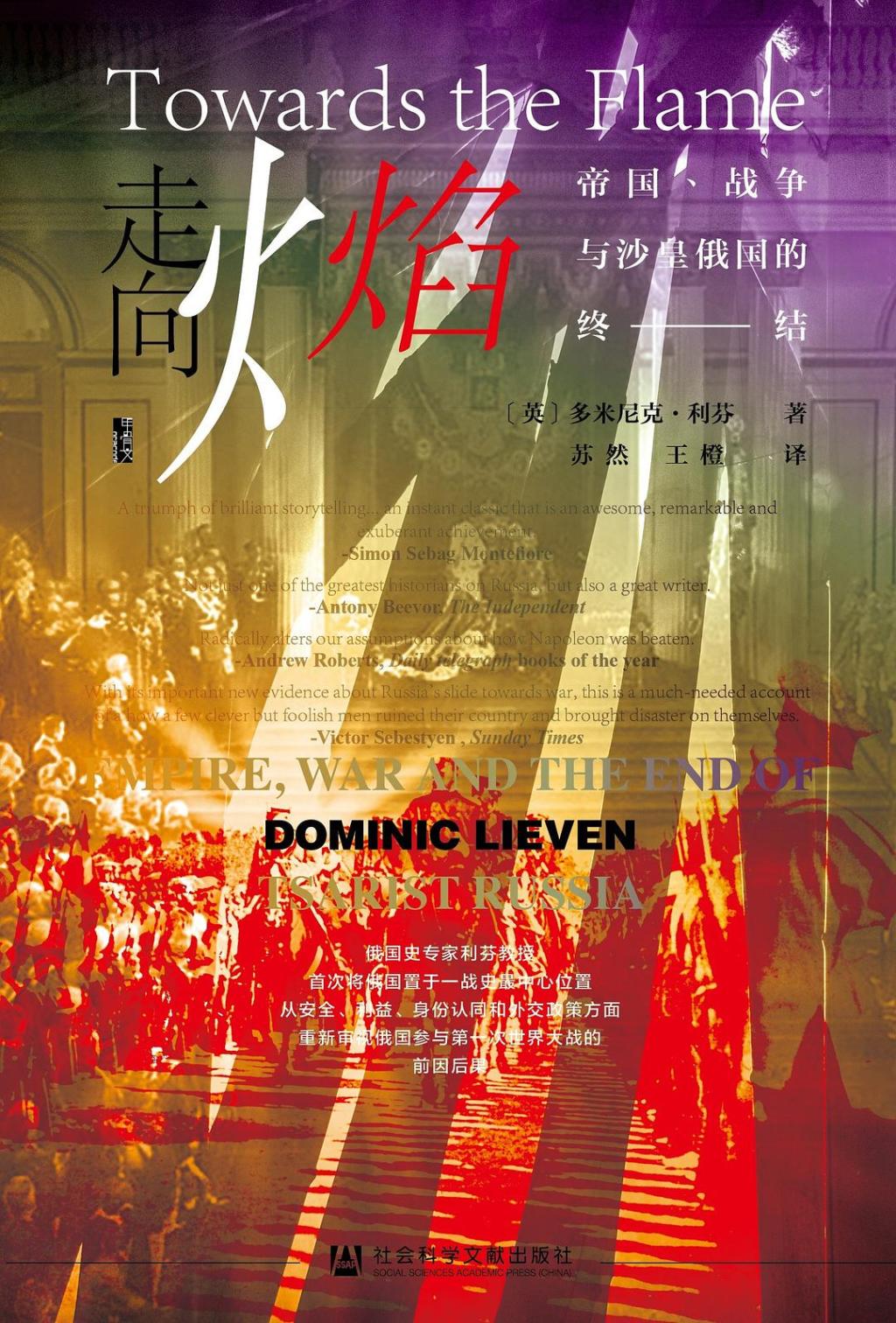
《走向火焰:帝国, 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中译本
同年出版的《走向火焰:帝国, 战争与沙皇俄国的终结》可以被视作是利芬第一部作品《俄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及相关研究成果在30年后的汇总与更新。与最初的作品相比,俄国史在一战研究中“最后的前沿”的地位已然改变——相关文献已可获取,现存学术成果也不可同日而语。利芬在本书中依然予“帝国困境”和民族主义冲击以理论中心的地位,他将东南欧民族冲突视为俄、奥矛盾乃至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分析方法上则继承了他对探究具体群体思想状况的偏好,也即他在前言中提及的多视角切换。利芬认为德国和奥地利仍然应该为1914年战争的爆发负主要责任,但总体上各帝国精英在面对地缘政治失衡和民族主义挑战时均作出误判,故一战既非不可避免,也非偶然的,以单一责任制去追究战争责任毫无意义,催生它的帝国结构性对抗已经暗示了20年后战争再开的必然。利芬在2016年以此书获普希金故居图书奖而接受采访时,表示写作该书是为了反驳为德国开脱、将一战罪责归于俄国的观点。他并未直言所指,但很明显他的辩论对象是肖恩·麦金(Sean McMeekin)在2011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起源》(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尽管《走向火焰》驳斥了上述的修正主义观点,但从结论观之,它对战争爆发原因、战争性质和地缘政治状况的解读,几乎重复了一战研究中的旧有结论,且在乌克兰问题和叙事视角等本书特意提及的要点上,利芬并未给出清晰及有颠覆性的呈现。不过考虑到利芬年事渐高和写作期间健康状态的急剧恶化,以及俄罗斯外交档案馆的关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都需要认可此书的独特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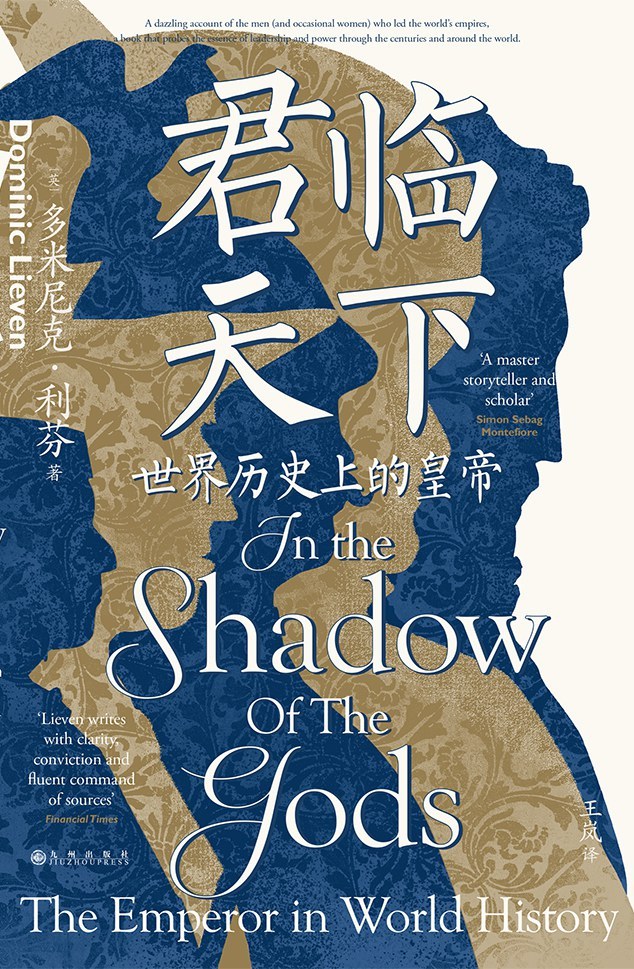
《君临天下:世界历史上的皇帝》中译本
利芬的最新作品是2022年出版的《君临天下:世界历史上的皇帝》,这是一部作者直言“不愿把其范围进一步拓展出我研究的舒适区”的作品,因为它的研究范围囊括了从阿卡德帝国到二战结束的世界上大部分重要的帝国,这一骇人的工作量逼迫利芬做出许多必要的删减,而即使针对本书有限的研究对象,500页出头的篇幅也显得相当局促了。利芬对本书寄予的期望是凝聚他所学所想的一切,意即封笔之作,我们很容易从“皇帝”这一概念中看到利芬过往研究成果的影子——皇帝是帝国的化身,也是对帝国结构和帝国竞争的人格化体现;皇帝亦是常人,个性和结构身份的矛盾会深刻影响国家走向;同时由于涉及面广大,书中大量运用比较法以探究各国“皇帝”概念的异同。本书通过帝国成败的对比,试图说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帝国如何形成,又如何凝聚。对利芬自己而言,这本书在对他原创理论的深化和适用范围的拓广方面都已达到了力所能及的程度,这已足够它在同类研究中脱颖而出,因选题而“力所不逮”的缺陷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利芬在研究选题、方法和观念上的回归倾向,背后是他充满时代色彩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以及他对家族史的理性思索。事实证明,对旧理论的反复思考,同样构成学术进步的重要步骤。
结语
包括利芬自己在内的众多史学研究者都曾经、或正在和史学中的政治学派做斗争,只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也依然委身于此。这番话并非对“历史科学”的完全否定,但随着历史主义的回归和历史研究新领域的蓬勃生长,范式化研究的缺陷在逐渐扩大,其解释范围也在相对萎缩。从这个层面看,利芬那个时代的学者正逐渐滑向“老一派”阵营。可若真如此归类,我们就依然在用机械的定义划分世界——事实是,我们视之为过时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时代往往是最具创新、开拓能力的群体;在2015年的《俄罗斯和拿破仑战争》文集中,利芬尝试将全球史视野融入自己的旧学说,他依然秉持着自己对新学术品味的严肃态度。利芬坚持的一系列学术方法,包括其“帝国范式”,在一个时代内体现了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在帝国史、贵族史、一战史等领域启发了后继学者做出更有颠覆性的研究,我们应当对这些成就给出高度评价。
当代俄国史研究已不再为“范式”所困,呈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与多样性,国别史的经典研究类目也逐渐通过全球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身份认同研究和众多跨学科视野与更广泛的历史观联系起来。但摒弃某种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无需再回头看向它们,相反,我们需要时刻直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直观上并不漫长的几十年时光已足够史学几经波澜且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也让几个世代的人们眼中的世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而更感性地说,它还轻而易举地囊括了一个人最好的人生时光——为某些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其思考,其远胜后世大多数人的智慧,其富含历史情怀的感性,均被埋葬在这文字组成的墓碑里,又因为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而被削平。这构成了历史书写的悲剧美,也说明了学术研究蕴含的勇气和信念。
这便是为何中国的读者仍需要回过头去阅读利芬及众多俄国史学者在近20年前的研究——我们需要摸索着历史研究的脉络去寻找未来的方向,并重拾对历史力量和人类智慧的敬意;更何况,他们的研究直至今日也无法被彻底否定,其中仍然有许多养分等待当代研究者去发掘和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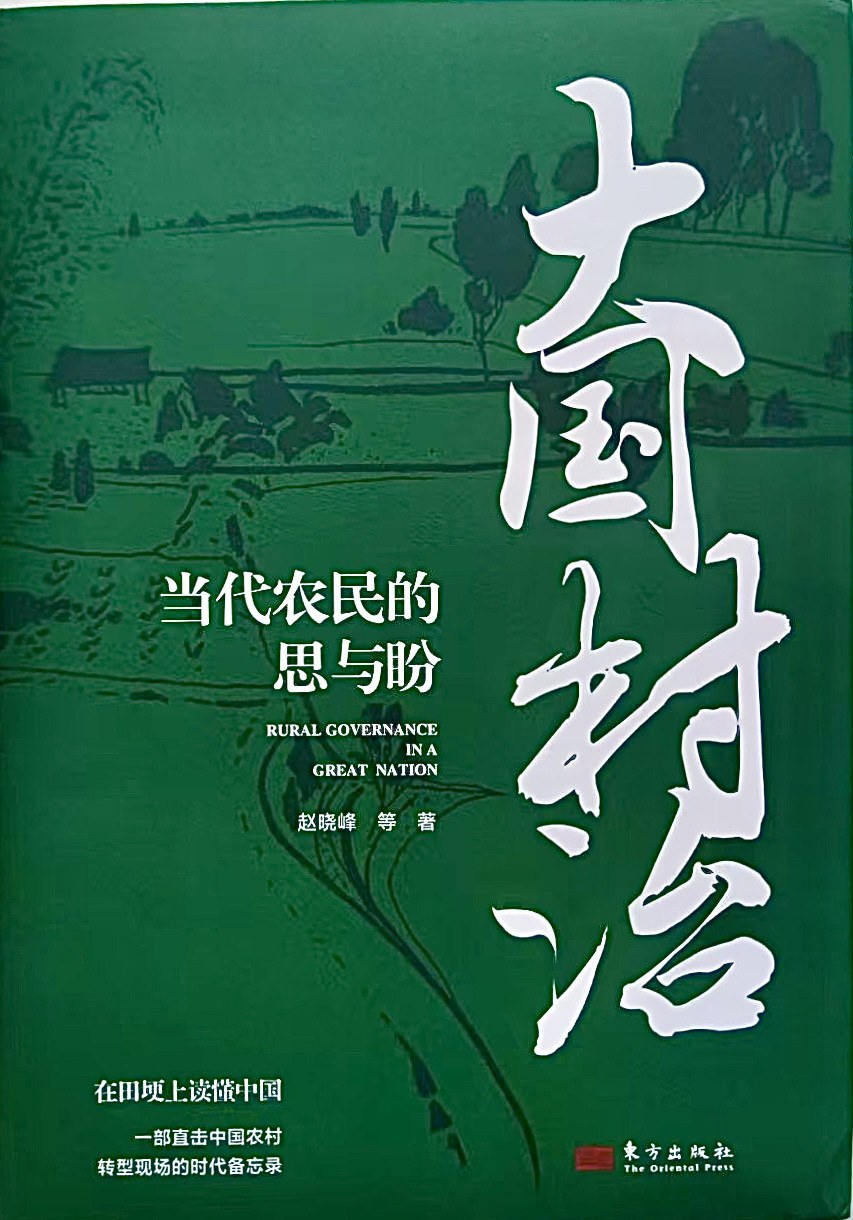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