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逃离孤独的时代,换言之,也是个倍感孤独的时代。
老年人渴望从短剧和直播中获得陪伴。青少年渴望接触网络,从流行符号中获得认同。青年人则在下班之余快速切换状态,渴望在另一种生活中找到归属。人们渴望被填满,去替换生活塞给我们的苦涩与空虚。虚拟偶像、AI陪伴、labubu、谷子……越来越多的事物正在被寄予更多的情绪价值。
但总有些时刻,那些断网的时刻、被迫等待的时刻、失眠的时刻,你不得不与自己独处,想要抓住什么却又掉进漩涡之中。每个人都仿佛身处时代的孤岛,渴望逃离却无所适从。
这个时代到底怎么了?我们为什么丧失了独处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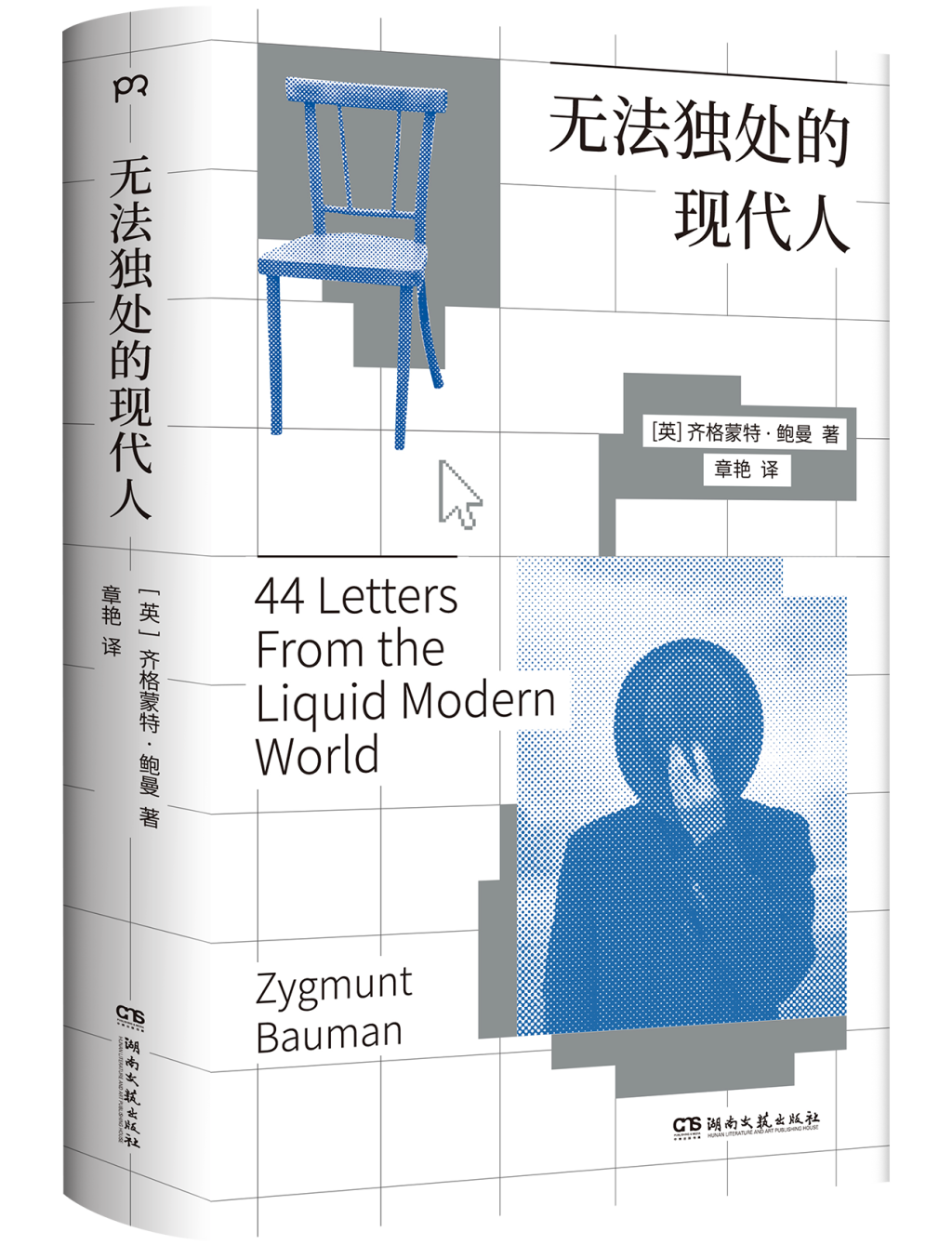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英] 齐格蒙特·鲍曼著,章艳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5年7月版
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当今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机:经济波动、技术膨胀、信息爆炸、知识焦虑、身份危机、心理疾病、消费盛行……它们都对人们的独处空间和生活节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这是一场流动性的危机,它隐藏在这个时代加速前行的表面之下,让生活越来越脱离我们的掌控,并将一种碌碌无为的不安植入我们的骨髓。
流动的时代
Y世代和Z世代,指的是1983年到2005年间出生的两代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80后90后,还有部分00后,他们现在的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这两代人最先感受着这个社会日新月异的温度,他们要么刚刚步入社会,要么刚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要么正在思虑自我和社会的关系。
与他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不同,他们身处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几十年前,社会还是“固态”的,它是长辈们口中那些晴朗冒汗的日子和笔直的公路,那是一个以工人和军人为代表的生产者社会。但如今,人们在几年间可能就经历了几十年的变化,没有人能够说清明天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会记住昨天的细节,一切都在“当下”这个微妙的时间点上爆发,又迅速流逝,这是一个以原子化个体为代表的“液态”社会。
经济会上行,也会下行;一个行业可以迅速崛起,也可能瞬间蒸发。即便某一次工作做得很好,但这种成功又能持续多久?技术正在快速迭代,我们手上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又能持续多久?终身学习,难道不是另一种焦虑的体现吗?信息和机会是在变得更多,但庞大的信息和机会本身似乎又变成了一种障碍,让我们无法更清楚、更坚定。
如果说现代性象征着自由、科学与创新,那么它在本质上便是流动的,无法被定位,无法被确定,无法被有效解释,换言之,它始终处于某种令人不安又焦虑的变化之中。
人们的工作、关系、爱好、身份、习惯,都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陷入某种无迹可循的境地。这种大环境的流动性,被内化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变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它煎熬着每一个想要独处,却又不得不疲于奔命或为生活殚精竭虑的人。如果生活不是在内卷,就是在内耗,躺平又怎么能真的实现呢?正是在这种摇摆不定之际,这个时代的两股浪潮向我们袭来。
无处不在的虚拟空间
无论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人们造成了什么其他影响,它无疑都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空间的感知。这一点在独处时尤为明显:我们往往偏好用“空间”来形容一个人独处的限度,仿佛它不被时间所困,而是固定地存在于心底的某个地方;但如今,这种空间的边界不再明朗,而是被稀释在漫无边际的虚拟世界中了。

2024年3月11日,一场扩展现实(XR)体验展在美国“西南偏南”大会和艺术节上举行,将参观者带入各种主题的虚拟世界。(新华社)
得益于电子媒介的便捷性,这是一门很难拒绝的买卖。曾几何时,无法实现的各种欲望如今都变得近在咫尺:与朋友联络、交际、玩游戏、看剧、购物,哪怕只是发呆,将自己悬置于虚拟世界里,也变得柔软又亲近。归根到底,是我们选择了虚拟空间,它是我们自由的某种象征。有什么比沉溺于自由的表象更能让人陶醉的呢?在无法掌控的世界中,虚拟空间让我们拥有了一些掌控感和归属感——所谓“独处”不也意味着这些吗?
欲望不会停止,它只会藏得更深。“潜意识”是现代最伟大也最值得警惕的概念发明之一,它取代“上帝”,成为人们脑袋里那个巨大而又诱人的谜团。“互联网”则紧接其后,它试图将“世界”与所有人的“潜意识”勾连,成为新的神话。虚拟世界,俨然已经成为某种群体潜意识的隐喻。换言之,当沉浸在虚拟世界时,我们不过是沉浸在某种潜在的欲望之中。
但是什么被改变了?鲍曼认为,在虚拟空间里,满足欲望的速度更快,代价更小,责任也更为隐蔽,人们不需要直面冲突所带来的负担,就像是穿上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轻便斗篷”。只要感到了压力与不适,你就可以退居幕后,取消、搁置,甚至转移眼前的对象或者事物,而不用需要费尽心思编造借口、道歉和撒谎。
这意味着虚拟空间与以往独处空间的一个关键不同:它难以忍受矛盾的真实性。作为现实生活最恼人的特征之一,矛盾、分歧、冲突和落差,持久地横亘在我们的欲望前。在独处中,没有任何遮挡、距离和快进,在你的目光和内心之间,矛盾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某种方式被忍耐下来;在一阵无法逃避的思绪中,身体渐渐蒙上了一层坚实的力量。而在虚拟空间中,矛盾要么被缩小,要么被放大了,经过一层滤镜之后,它或多或少会失去原本的意味,变得有些轻浮、空洞、无法忍受——欲望的满足不应该是毫不费劲的吗?
虚拟空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鲍曼看来,独处应当是“一种美妙的状态,可以让你整理思绪,去沉思,去反省,去创造。最终,赋予交流以意义和实质”。(14页)
一种被消费定义的生活节奏
电子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消费市场和它所奉行的文化的发展。如果说虚拟空间仍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那么虚拟空间中的消费文化则是人们被迫接受的一种观念。
仅仅十几年前,互联网还和超市一样,人们直奔目标然后离开。这是一次主动的、有计划的、依据需求的动作。但如今,正像人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拿起手机,消费也往往源于一次意外——只因不经意间刷到了某个推广……
比起按需购物,意外的消费能为市场赚到更多的钱。而为了制造这种意外,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推广。何况事到如今,如果一个商品根本不做任何宣传,那它根本走不到人们的眼前——眼下已是铺天盖地的广告。当“流量”本身成为一门生意时,人们的注意力/虚拟空间里的每一处早已在暗中被定好了价格。我们无法得知互联网和市场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下了多大的功夫,正像我们也无法得知我们的网上冲浪或是线上消费,在多大程度上仍是主动的、有计划的、依据需求的动作。
但是比起生产者社会,消费者社会为我们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我们可以更自由地开发自己的兴趣,无论我们如何定义这种“自由”。问题仍然在于,什么被改变了?
在鲍曼看来,消费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将人们的生活拖进一种失控的节奏中。既然消费市场的逻辑不是满足你的需求,而是不断为你创造新的需求,那么它就会让你始终处于满足而不得的状态中。简言之,消费主义的要诀就在于,让你花钱也买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因此受消费所困的人始终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他们不仅仅为消费不起而焦虑,也为不知道该消费什么而焦虑,更为消费后的不满而焦虑,因为总有新的商品正在上架,总有一些“需求”迟迟未得到满足。这种微妙的心态正如鲍曼所言:“你之所以烦恼,是因为其他人发现了能带给他们满足感的新发明或新发现,而你却错过了它们出现的时机,因此潜在地被剥夺了这种满足感。”(111页)

2023年11月10日,备战“双十一”。(新华社)
正像消费会促进生产,消费主义也会助长一种效率至上的文化。如果你既没有在赚钱,也没有在好好地花钱,那你的生活就会变得乏善可陈,因为这意味着,你既没有满足自己的“欲望”,又对你本该有的欲望没有欲望。一种停滞不前,或者只入不出的生活,是没有被社会好好探索的,整个社会被充分宣扬且强调的只是一种被消费(或生产效率)定义的生活。一旦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工作,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去生活。仿佛生活只是工作-消费的橱窗,而独处不过是其中一段没有“效率”的空窗期。
最终,你感到没有空间,即便你正一个人独处。
因为你失语了。你被剥夺了对自己和对自己生活的定义权,被解释、被分享、被展示、被标签化。这个时代的潮流正急于冲刷你的生活,让你成为流动(流量、流通)的一分子,以助长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独处空间”倒成了一种阻碍,因为它不够公开、透明,无法被计算。
但人之所以是一个具体的人,就在于他不够公开、透明,无法被计算。我们一面苦于自己没有个性,一面又为不能成为群体的一员而隐隐不安;我们一面希望定义自己,一面又不希望这种定义太过清楚;我们一面寻求快乐,一面又觉得这快乐太过轻易……人之所以是一个具体的人,就在于他内含矛盾,而又铿锵有力。
曾经只有艺术家和贵族,或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才具有的种种欲望,矛盾、空虚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戏剧性的外在环境,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可以说,在这个时代,生活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
而正像鲍曼所言:“所有艺术都留下了斗争的痕迹、胜利的痕迹、失败的痕迹,还有许多虽然迫不得已但仍然令人不齿的妥协痕迹。” (296页)生活的艺术在于抗争,更在于那些抗争所留下的痕迹——“真正重要的是自我定义和自我表达”。(295页)
或许,现代生活的复杂之处不在于独处空间的消失,而在于独处空间中矛盾的多样性。每一次清醒地意识到矛盾的时刻,都是一次思考、阅读、书写、对话自己生活的时刻。在挣扎中,我们纵使赤裸、脆弱,却忠于自己,不再孤单。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