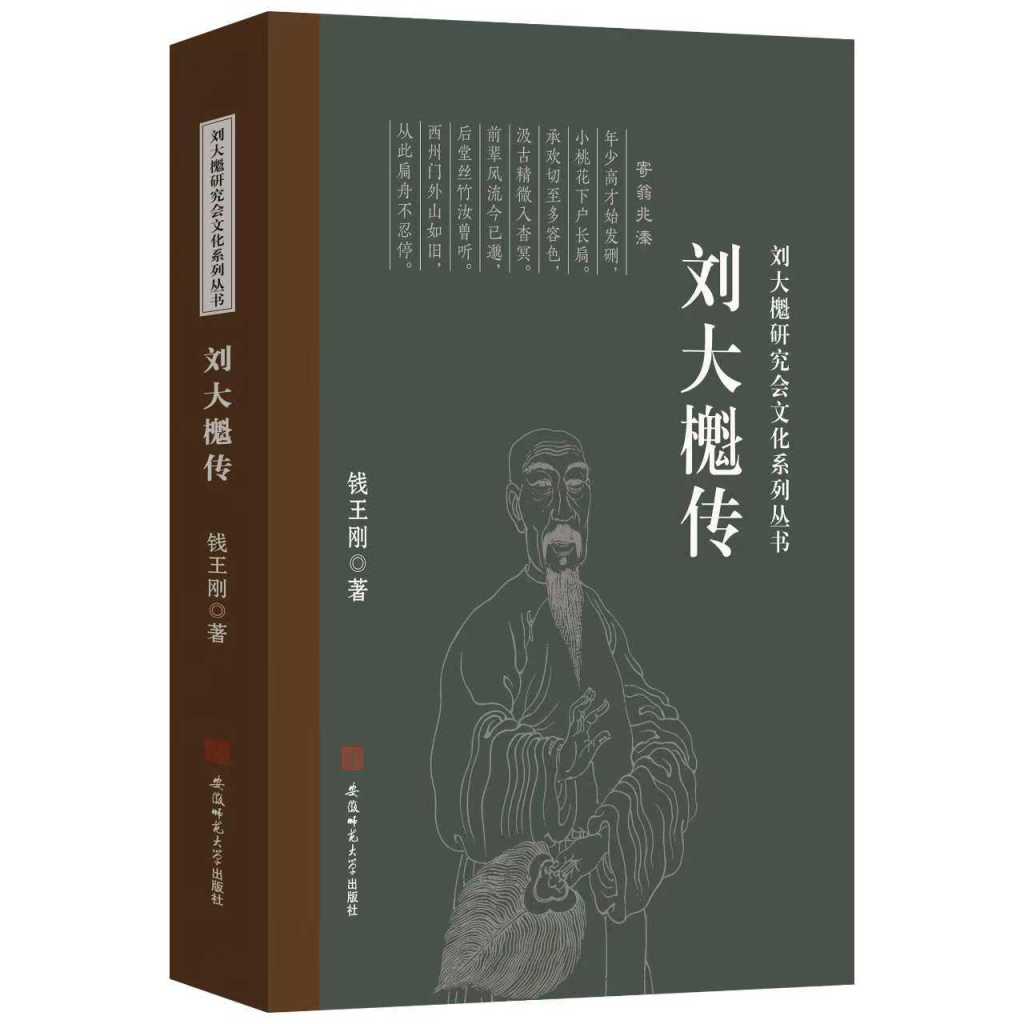
《刘大櫆传》,钱王刚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版
为历史人物作传,确乎不易。其难处大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献材料方面的难处。这一方面的难处大致又分为两点。第一是缺材料。这表现在很多历史人物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并非有显赫的名声,时人也未必多有关注。因此有关这些历史人物的第一手材料就有可能留下得不多。当人们回顾历史,发现这些历史人物当时虽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其身后的影响却慢慢大起来。为了说明这些历史人物何以能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就需要追溯其生活的具体细节,为他们立传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这时候,人们发现,为他们立传又是很难的,因为缺少第一手的材料。第二是文献材料要辨别。有些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起伏不定,本人留下了很多材料,如日记、通信、著述等,以及时人对他们的看法。为这些人物立传就有材料辨别的困难。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得到了时人非常多的评价,而且这些评价方向不一致,那么选取合理的评价无疑就存在难处。除了时人的评价,历史人物在各类史志文献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真实性往往值得推敲。辨别这些文献也有相当的难处。
二是历史人物本身带来的困难。能够成为历史人物,大多数经历都很丰富,交游相当广泛,思想也一定有多角度的阐发。从传主的角度说,他们未必承望后人为他们作传。因此不会有某个人从小就准备着把自己的生平材料留在那里,等着百年之后有人为之作传。更有甚者,有些历史人物要么自诩甚高,要么有很强的历史意识,他们在世的时候就为自己做了自传。因为自传多少带有传主的自我选择,有可能会出现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其完整性、真实性往往难以保证。对待这些历史人物,后人要想写好他们的传记,其难度就变得更大。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如何描写这些人物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如何深入他们的内心,去描写和表达他们的精神世界。而这又是传记作品中最难于表达的部分。
当钱王刚先生将《刘大櫆传》发给我的时候,我拜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就深感作者创作的不易。虽然和作者只有一次面缘,但是通过对其文字的阅读,我却感受到作者内心世界的丰富,以及他对桐城派文学和桐城地方文化的热爱之情。
在我和作者电话交流的过程中,就传记题材的文字作品如何撰写的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钱王刚先生也认为传记写作有难处。他认为传记难写,历史人物的传记又甚之。首先是材料要做到“真实不伪”。真实需要更多地掌握资料,需要作者投入更多的研究精力,真实也容易束缚一般底气不足的作者的手脚。其次是表达要“准确生动”。准确要在研究与真实的前提下,对人物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表现叙述要合适得体、精准到位,力求写什么是什么,不可夹杂主观好恶。方苞的《孙征君传》为人所称,然写一个大学者,只叙述其品格,而于学问简略不提,便是不准确不得体的例子。中国作协近年组织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有一剧作家著《王阳明传》,关于阳明学说的叙述只有极小的篇幅,就有失偏颇。针对钱王刚先生的上述观点,我深表赞同。
钱王刚先生在创作《刘大櫆传》的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确立自己创作的思路。他说写《刘大櫆传》,需要总结传记古今创作经验以及自己以前所写二传之得失(钱王刚先生之前著有《方以智传》《钱澄之传》)。其中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如何克服传主生平不清楚、经历简单平淡的困难,既将其真实完整的生平叙述明白,还要通过文学描写,尽力去表现和塑造一个才志不凡却经历坎坷苦难而又抗争不屈的人物品质与形象。二是兼顾传主作为诗人、古文家以及学者的多重身份,尤其要聚焦其在桐城派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贡献与影响,勉力去作多方面的探讨展示。钱王刚先生非常自觉地检讨自己写作《钱澄之传》时,所表现出的重其诗文而略于其治学与学术贡献的缺点。
这种谦逊的学术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其实钱王刚先生在创作《钱澄之传》的过程中,对很多因陈已久的流行的观点就进行了辨析。如方苞在《田间先生墓表》中就曾经说钱澄之北归后杜足田间课耕自给,俨然是一个隐居乡间闭门不出的遗逸。钱王刚针对这种说法作了大量考证和阐述,指出钱澄之不仅没有杜足田间,反而是数十年风尘仆仆,不忘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四处奔走。
正是这种自觉反省的态度,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促使《刘大櫆传》的创作呈现出很多新的面貌。钱王刚先生说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除了研究熟悉人物生平与资料,还本着阐明传主的文学思想以及乡土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写作中尽可能避免内容表达与行文的干涩僵硬。为此《刘大櫆传》做了几个以前未做过的尝试。
一是夹叙夹议,也就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尽可能把每一个问题讲深讲透。如作者在考证刘大櫆出生地这一问题方面,就充分运用了多种史料。“大櫆自然出生在他父母包括祖父母一家所居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因后来大櫆本人没有明说,其他史料也不见记载,后世便有根据其曾祖隐居合明山而指其诞生于彼的看法,这是失考不确的。欲知大櫆的出生处,尚须做一点细致分析。”作者既讨论了刘大櫆祖父刘日耀隐居合明山的历史,对刘大櫆父辈三兄弟析家分居的情况也做了考证,最后引用了传主本人的诗,“余生黄炎后,家世本农人……长夏往南亩,遇事皆可欣。田禾际渚草,瞻望碧无垠。”“出户步除阴,兰芽亦已长。鱼依曲岸浮,鸟溯青霞上。”作者认为这都是说他的家居,是在水畔。这是怎样的水畔呢?“相看无一言,湖水当门碧”,“湖水日当门,青山澹无语”,原来他是居于濒湖之地,家门的前方便是碧波荡漾的湖水。作者的结论是刘大櫆出生地应该在湖畔芮庄。这种史论结合的方法是让人能够信服的。
二是化史入叙,对历史材料不是简单地堆积排比,而是化作叙述的材料,以丰富传主的形象。作者在写传主受本土先贤影响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介绍,而是以简略的叙评之语交代刘大櫆成长过程中心路历程的变化。如写刘大櫆跟随吴直学习的过程中,非常敬佩吴直不喜八股、偏爱诗文,对吴直抱有较为激进的学术观点也常常表示认同。作者写道,“其(指吴直)思想态度如此,可以想见他于合明山中执教课徒时,势必会谆谆教导他的学生,要做一个古之君子那样的纯粹之人,不与功利虚伪丑陋的时俗随波逐流,以正确的心态与学风去治经学习,努力做一个正学善学而有益于世的真正读书人!这种教育,对于学生们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只是此时的社会环境下,老师的教诲意见肯定是有些人听得进去,有些人听不进去,有些人入耳而未入心,有些人则记忆深刻难忘。十四岁的大櫆,显然便是这后者——他日后关于读书治学包括对儒学经学的态度看法,除了少数地方与乃师有着明显区别与分歧,大多是吴直的翻版;有些方面,虽面目有异,然也是缘之师风而变化。”这类叙述不是凭空议论,而是帮助读者更为深入地了解传主独特的人生经历,也为读者更好地把握传主的思想取向提供了参考。
三是改绍介评论为活泼叙文,将传主的文学态度与主张化成寻常的对话来表现,较之大段的平铺绍述则效果不同,姚鼐问艺一节便如此。我们节选一段,读者可以先睹为快。
姚鼐说:“我朝自康雍以来,古文复兴,嗜好者众,号称能者亦不少。然据学生阅读体会,作品多属平凡而精彩迷人者极少,可为借鉴启发者更鲜寡,让人怅惘且感叹!”大櫆道:“其实非仅本朝如此。明人倡复古文,张口闭口诗古文辞,可除了少数方家,如今人所仿效学习之归茅辈,你看当时文坛上,又有多少上乘传世的佳作?”姚鼐惑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作者缺乏天赋才能?抑或是文运不兴,以致文坛世衰不振?”大櫆沉吟一会,道:“这里面的原因,颇为复杂。汝说的天赋文运,自然都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世无其才,文星自寥,而有才无世运,亦难振兴。但在我看来,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因,影响古文创作甚大……”“愿听,请老师喻教!”
一步步被引入文学深处的姚鼐,闻听之下激动不已。而接下来,他便听到了一番为他打开古文创作新视野的议论。这就是刘大櫆的神气说。这种对话式的描述,一改平铺直叙的陋习,让传主在读者面前变得更为鲜活。对话式的表达,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便于读者更好地领会对话双方的观点。刘大櫆的文学主张不知不觉间就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这种借助对话来叙述传主思想的细节,丰富了传记作品的表达方式,富有新意。
以上三点突出体现在钱王刚先生创作的《刘大櫆传》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细加品味。就这本传记创作的总体过程来看,作者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据作者介绍,他在创作初期,拟出了二十章二十万字的初稿。但是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作者又不断增加章节,扩充内容,形成了第二稿。之后在修改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传记所述与目标要求,复又对其中几个章节做了大幅的调整修改,成了现在的模样。应该算是三易其稿吧。
在准备和写作过程中,作者又从各个途径查阅史料。凡遇某时某事某人有不清楚的,便放下写作去查找资料,以明确写作的方向。其中在谱载与方志史料方面,除了查阅陈洲刘氏宗谱及传主所在房支的家谱外,还因着传主的交游所涉之人物,或自己查阅或委友人查问谱记。这些资料涉及桐城当时望族桂林方氏、高甸吴氏、清河张氏、麻溪姚氏、宕里左氏、项家河叶氏等。方志则包括清桐城县志、歙县志。此外,作者为了写清楚传主在雍乾时期所涉人物情况及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相关事件,反复查阅雍乾二帝实录,以求实证明确,不为虚文臆断。读者阅读本传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这些资料的搜集和展示,也为后续学者研究刘大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这样的传记不仅有文化传承的价值,还有学术参考的价值。
刘大櫆作为桐城派三祖之一,生活于方苞和姚鼐之间。对于桐城派来说,方苞是一个奠基性的人物,其早年虽然因为《南山集》案入狱,出狱后以程朱理学为宗编修《钦定四书文》,开启了桐城派和桐城文的端绪。刘大櫆继承了方苞的学术衣钵,寓居京城期间写下了《游大慧寺记》等散文,充分展示其独立反思的精神。刘大櫆因科场不顺,日后以教谕培养后学为任,培养了大量人才。姚鼐师从刘大櫆,也在继承乃师学术精神的基础上,编写《古文辞类纂》确立文体分类标准。到姚鼐这里,桐城派和桐城文的理论可谓基本成型。这一学术发展的脉络,在《刘大櫆传》中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如果说刘大櫆的生平经历是这本传记的外显的线索,那么刘大櫆承上启下的学术思想发展则成为内隐的线索。这两条线索相经纬,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文人形象,一个值得后世不断揣摩深究的学者形象,一个桐城派形成时期关键人物的形象。对此我们也可以借助传文的内容作一粗线条的梳理。
早在十几岁时,刘大櫆随吴直学习,就已经表现出文学方面的天赋,开始展示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吴直归里后,刘大櫆兄弟在家自学。这个时候的刘大櫆开始对自然万物、社会人生进行自觉反思。“这个智慧而有思想的少年,于田事农作歇息之余,又或释卷漫步之际,时常会对着广袤沉凝的山水大地、苍冥深邃的高天星空,以及侵临感官的万千自然与生命的气息,独自怔怔地陷入沉思,如同古往今来许多为之而迷茫困惑的智者那样,在脑海心底禁不住一遍遍地发出疑问。”为此刘大櫆创作了《辨异》一文。
通过分析这篇文章,作者指出刘大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从《辨异》的文字可以看出,“没有什么上帝或神的创世,所谓鬼神亦不过是天地的化育现象而已;我们身外的宇宙和世界,都是客观的存在,是太极阴阳五行运动变化和人类性情生活需求发展之结果:有天地自然,而有万物人类;有人类之生活争乱,而有国家社会与文明文化之形成。这样的认识,是与数千载以来包括知识界在内的世人普遍迷信超自然的力量,并将天象灾异与人世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天人相感的思想观念明确对立的。它在尊重客观存在并隐察自然与人世各循其规律而发展的基础上,将天道与人道区分开来,并明确地宣称:即使圣人(人间帝王),亦不能干预人民‘天之固有’的生存生活权利!”“一个年轻的学子,却在探究天地大道的过程中,凭着‘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的洞察睿见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对程朱理学的权威予以质疑,更对其荼毒社会最深的人性论主张提出挑战。这是非常可贵的精神品质。
虽然此时的刘大櫆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但彼时的自学和之前的私塾学习不可能有系统的教学安排,因而刘大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就带有个人色彩。此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心知》,其思想观点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意味。对此钱王刚先生指出,《心知》中所谓“盈天地之间,皆吾心也”,不过是儒家与心学“人者天地之心”“宇宙便是吾心”的翻版衍说;而通过去除感官干扰昏昩,让人的心灵中正无妄、精神敛约至空明之境而可感知一切云云,亦是类如禅定壁观、宣称“意之灵明处谓之知”、倡言所谓“至诚之心”的阳明心学的具体解读与应用而已。
刘大櫆的思想为何会转向主观的一面,而不顾及客观的事实呢?作者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钱王刚先生认为:早在王学盛行之际,包括故乡在内的学者先贤们便看到了阳明“致良知”之说会导致不学空虚之弊病。如方以智就于批判中提出了“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口号。为何此际的大櫆,正当人生求学长知识的青春年纪,却写出《心知》这样的文章,要学那位阳明先生,去那灵台方寸之间寻求神秘唯我的真觉和至诚呢?深入地分析一下,它是否与《南山集》案的影响所导致的风气之变尚有关联?——当时政与经世的关注可能会招来无妄之灾时,读书人出于谨慎保护的心理,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治学求知的视线途径,由外在的学习获取更多地转向内在的修省提升。后来,因大櫆于自己治学极少谈论,偶有所涉也只鳞片爪语焉不详;而其思想观点与治学倾向,亦只存于为数不多的文论杂著中,给人以浅薄之感。故世人多有讥其学养不足者,这自是时代偏见所致的失允之论。然有一点,他读书不甚丰博,治学也惟重要理大义之洞明,却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根据钱王刚先生的阐述,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桐城派和桐城文之著名于世,更多是其文章,以及文章创作的理论,而不是思想方面的创新。其中只有方以智是一个例外。
当然,刘大櫆显然也非常清楚程朱理学对于举业的重要性。任何想通过举业获得向上机会的年轻人都不可能不顾及这一点。刘大櫆虽然不喜欢朱熹的理论,但是为了举业,也必须了解和掌握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刘大櫆对北宋五子的思想产生了兴趣,尤其是重视张载的学术观点。钱王刚先生分析了刘大櫆这一时期的文章,特别对其《观化》一文做了评论。
大櫆的《观化》一文,应便依此清浊之说而论物之殊异。而这个承自于张载的“气质之性”,后来更是常被他挂在嘴边:在为他人所作的序文中,他往往据此而议论人物的天赋与文字,言之凿凿而不疑。可以说,张载的思想观念,在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认识论方面,都对年轻的大櫆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日后在对待和认识世界事物上,所持朴素的唯物辩证态度,不信鬼神之说等固与此密不可分,即其在有关人性、社会问题认识以及治学方面的一些意见主张,亦同样可从张载学说中找到思想认识的来源。甚至还可以说,他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受到了张载的明显影响。
从刘大櫆对张载思想的重视可以看出其思想主张是多元的。刘大櫆早年对心知的阐发,到对性理之说的反感,再到欣赏张载的气质之性理论,这种思想的变化说明刘大櫆并没有给自己确立一个终身服膺的哲学主张,这也是他最终没有走上哲学思想创造者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精神的世界中,刘大櫆更为关注文学的使命和价值。这就是他继承方苞,又有所独立创造,最后启发姚鼐,为桐城派和桐城文的最终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这一点在《刘大櫆传》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对此进行了描述。
方苞倡导的义法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综合,对于文章学的发展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刘大櫆接触方苞的义法说后,并没有盲目地信从,而是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这种对文学理论的探索也体现了刘大櫆精神世界复杂性的一面。作者在《刘大櫆传》中说:
方苞之义法说,以内容与形式的调和阐述,不仅融合了前人文道合一的文论,也总结了古文写作的基本方式与标准。是对文章学的一个创新贡献,于古文的现实创作,有一定的启发规范作用。故自提出后,也赢得了不少人的称许肯定。但他新认的门人大櫆,于他这义法之说,却似乎并不太赞同,二人谈论越具体深入,双方之间的歧异便越明显越多,而大櫆也颇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因先生的主张而改变其态度观点。
对此作者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
方苞虽将文章的内容形式的关系喻作经纬,义法互不可缺,但在实际上他更偏重“义”,认为“有其理而法自随之”;而大櫆尽管也承认义理在文章中的作用,但却更重视法度,探讨古文的创作规律与技巧,谈论他所谓的“文人之能事”。
方苞认为古文的写作,是本于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所以要写好古文,前提必须学好经学,得其义理;但大櫆虽也说“读书穷理”,却于经学并不如何深研,他更多的是出入诸子与历史。
方苞认为必须洞乎于义,始能暗合于法,义为法之根据,法为义之表现。所以他于义法之外,又有“雅洁”之要求,以追求古文之朴质和气洁。而大櫆对老师说的这些似乎并不太上心,其论文与言语,更是常常离开方苞片刻不忘的“义”去谈论,说什么文人之能事,只在神气音节中求之;至于语言,他更持一种较开放的态度,认为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臭腐?所以为文“贵去陈言”,要像韩愈那样,勇于创意而自铸新词,以适用于时。
这些辨析,为后文姚鼐问艺一章对神气音节说的阐述准备了前奏。限于篇幅,此处对刘大櫆和姚鼐师徒讨论神气音节说的细节不再予以赘述。读者尽可以去阅读姚鼐问艺一章的精彩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钱王刚先生在《刘大櫆传》中,没有囿于陈说,而是就刘大櫆学术思想的发展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钱王刚先生通过对刘大櫆早年从学的吴直,以及刘大櫆的学生的一些学术主张的考察,进而指出刘大櫆学术思想的传承并不是单线的,而是有着多条线索。其中吴直,以及钱澄之对刘大櫆神气音节说的影响也非常大。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需要加以注意。
以上,我们从《刘大櫆传》创作的特点,以及传记本文的叙述线索的分析,较为粗线条地阐述了这本传记的特点,以及对于传记文学所作的贡献。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是抽象的存在,其一生的活动都是由大量的生活细节构成的。这些生活细节又进一步形成了其人格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物来到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形成其独特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又都在一定的时空中展开。换言之,一个人的人生,就是其绵延不断的生活所填充的时空。当历史人物远去了,我们追溯他的人生,就是还原他曾经生活过的时空。
《刘大櫆传》洋洋洒洒几十万言,既对传主的生平事迹作了全方位的展示,也对传主生活的那个时代作了多角度的描写。其所展现的人物是具体的、鲜活的、生动的,是值得后人敬仰的、纪念的、品味的,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去回顾,去深入地探掘其精神世界中尚未敞开的一些内容。至今为止,刘大櫆先生的全部文集还未见面世,学术界对刘大櫆学术思想的研究也相对不足。这种局面与刘大櫆先生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我相信随着钱王刚先生这本《刘大櫆传》的出版,一定会吸引更多的研究桐城派和桐城文的学者去关注刘大櫆。作为一名出版人,我也真心希望能够早日见到《刘大櫆全集》的出版,看到更多的有分量的研究刘大櫆的作品问世。
我的祖父出生于桐城,八岁时随他父母迁居皖南宣城。我所出生的村落居民也都是由桐城迁入的。熟悉的桐城乡音,以及耳熟能详的桐城故事,从小就让我对桐城派和桐城文心生向往。读大学期间,我还专程到桐城故地探访祖居地。安徽师范大学的同事王少仁博士有一次遇到我,说枞阳刘大櫆研究会准备出一本书,请我们出版社予以支持。之后我便和刘大櫆研究会的前任会长刘继承先生取得了联系,然后就和钱王刚先生结识。钱王刚先生和刘继承先生是多年的老友。受刘先生所托,钱先生花了近5年的时间创作了《刘大櫆传》。期间我带着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又去实地考察枞阳刘大櫆研究会、海峰纪念馆等处。
钱王刚先生写完《刘大櫆传》后,出版社安排了我参与审稿。在审读的过程中,我深感刘大櫆在桐城派和桐城文形成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感受到撰写刘大櫆生平传记的不容易。这方面前人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从生平经历与思想发展的双重角度还原刘大櫆的人生,仍然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
最后,我以刘大櫆先生的一首诗《寄翁兆溱》作结:
年少高才始发硎,小桃花下户长扃。承欢切至多容色,汲古精微入杳冥。
前辈风流今已邈,后堂丝竹汝曾听。西州门外山如旧,从此扁舟不忍停。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