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莫言与王振共创的随笔集《放宽心,吃茶去》首发,在直播间里,莫言、王振和主持人杨澜一起,畅谈了这部从真实生活中来的随笔集创作背后的点点滴滴。
《放宽心,吃茶去》全书分为五章,是莫言首部记录生活小确幸的随笔集,这本书集散文、诗歌、书法、摄影于一体,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在努力拥抱生活、随时分享哲思的有趣的莫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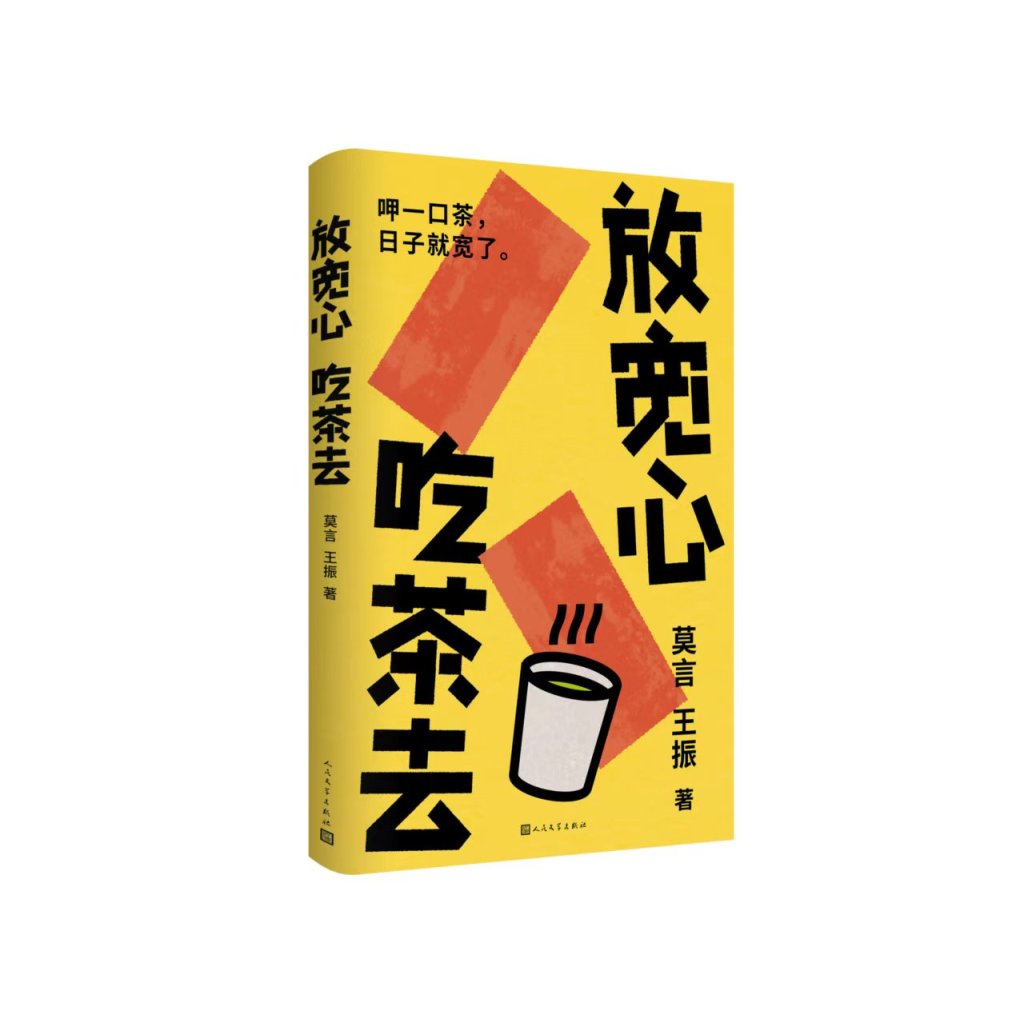
书影
发现日常、思考日常
山川湖海、市井烟火在《放宽心、吃茶去》中定格。
在山东,莫言在胶州的土地上学习用拖拉机割玉米,酣畅,但汗珠不再砸在镰刀上。面对机械化劳作的效率莫言感叹:弯着腰的痛苦,只有弯过腰的人才知道,而直起腰来的幸福,也只有弯过腰的人能体会。
在湖南,江水悠悠,暮云飘动。莫言游凤凰古城,赏沱江晚景,写下:在凤凰的石桥上,看沱江里的暮云,满头银饰的少女镶嵌在云里,梦里,人与桥动荡不安,还有什么不能释怀。
在英国,莫言参观了狄更斯故居并手书狄更斯名言:人要像牡蛎一样,神秘、自给自足而且孤独。原来孤独是如此具体的存在,是人们胸腔里缓慢开合的贝壳;
在肯尼亚,马赛马拉的土扬起热风,金钱豹的斑纹在草丛间忽隐忽现。莫言荒原逐兽,追记:君子思豹变,莫忘初始心。路在常理外,举火苦追寻。豹子成长过程中,要经历皮毛从斑驳到光亮的磨砺,真正的蜕变,从来都在常理之外的荆棘路上。
在希腊,莫言记下阿波罗神庙前的石壁上古希腊先哲们留给后人的三句箴言:一,认识你自己;二,凡事勿过度;三,承诺会带来痛苦。这三句箴言,静静凝视着世间的风云变幻,向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后人传递生活的智慧。

莫言在大秃顶子山
相比于宏大记叙,《放宽心,吃茶去》更关注小事中的体悟和感动。
莫言再登岳阳楼时,回忆起十年前初登此楼,一老者与莫言打招呼,不慎失足磕到门齿,又有稚童十数人邀他签名合影。如今凭栏远眺,莫言发出感叹:想那老者门齿已补,孩子们也都考上大学了吧!门齿的脱落是意外的,孩子们的热情是鲜活的。这些细节像生活本身一样“未经修饰”,让十年前的回忆有了真实的质感。
“好日子”不是一个遥远的、完美的结果,岳阳楼前对过往小事的惦念,是莫言最朴素的生活瞬间。

莫言与王振
一场关于“放宽心”的对话
直播中,杨澜与莫言、王振的对话围绕书中的主题——“放宽心”展开。
《放宽心,吃茶去》的书名,源自莫言因柏林禅寺未开、只能在门外遥观时创作的诗句“放宽心境吃茶去,大义微言梦里寻”。莫言没有执着于入寺的结果,而是将寺外所见所感转化为创作灵感。当莫言在颐和园刻意拍月未得满意作品时,他也写下“钓来东海一轮月,照我蹒跚夜路行”,不困于没拍到好照片的遗憾,转而捕捉过程中偶然涌现的诗意。
莫言在现场分享道,这两个故事共同表现了“放宽心”的本质:主动接纳世界的不确定性,与生活和解,让过程本身成为滋养生命的力量。莫言说:“就像猎人打猎,不一定每天都有收获,但过程本身就有意义。”

莫言在活动中
杨澜以普通人的困境提问:“今天份子钱都没挣够怎么放宽心?”直指“放宽心”在现实压力下的奢侈感。
莫言回答:“你没放宽心也是挣不够,事情已经发生,紧张焦虑都于事无补。不如放宽心,喝杯茶,冷静下来想办法再绕一条路”。他认为,“放宽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接受不如意、调整心态的能力。生活中的困顿与遗憾不会因抗拒而消失,与其在情绪内耗中放大痛苦,不如先承认此刻的状态。“喝杯茶”的片刻停顿,实则是为绕一条路积蓄心力。
分享会中,谈及让莫言感到最亲切的古代文人时,莫言说最想在梦中相见的是李白。“李白无边无沿蓬勃的想象力,放浪不羁的精神状态,潇洒的人生态度,这都是令历代文人向往的。”
“如果真的像他当时想象的那样出入宫廷、高官厚禄,恐怕也没有后来那么多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的诗篇了。”在莫言眼中,李白的放浪不羁正是一种“宽心”,他在逆境中舒展自我的力量,面对命运无常依然保有对世界的热爱与创造力,传达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

莫言拥抱3000年茶树王
【原文选读】
《摄月小记》
黄昏入园,急行至十七孔桥边候月,但东边天际有朦胧雾气,又有霓虹闪烁,令人担忧。直至八时十分,暗红的月亮方从林木间露出脸膛。东边天际依然晦暗模糊,虽费尽心机,也未拍得一张满意的照片,此时看园人厉声催促离园,只好怏怏而退。由此可见,心想未必事成,无意之中得到,也许就是最好的。对于摄影来说,尤其是这样。
正如俗言所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行。世间多少好光景,犹如黄粱梦一场。
《游泳与书法》
我对锐意创新者一向敬仰。许多现在看起来离经叛道、不被接受的东西,将来有可能成为后人眼里的经典。现在最好不要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但创新者也应研究创新的规律,即创新其实是量变的积累,另起炉灶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书法领域的创新更是如此。
吾在小说创作领域,一直锐意求新。但近年愈来愈感到小说技法其实并无严格的新旧之分。无论如何新,最基本的东西还是必须遵守。书法大概也是如此吧。我是业余爱好者,不敢妄言,泛泛浅见,供方家两哂耳。
《九龙皇帝涂鸦大师》
他的书写行为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刚开始人们反对他、举报他,警察训斥他、拘留他,但只要放了他,他就会提着墨桶上街。政府不得不雇请专人用油漆覆盖他的墨迹。而覆盖后的墙壁或廊柱更激发了他的书写欲望,渐渐地,人们习惯了他、接受了他,他的书写成为了行为艺术,成为了文化现象。
时间与执着的坚持,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厌恶变成了尊敬,嘲弄变成了同情,人们渐渐地意识到,这个看似癫狂的小人物迹近荒唐的行为,似乎具有某种深刻的象征意味,这行为与历史记忆、殖民统治、家族传承、个性自由、底层文化等都有着某种关联,他并没给社会制造太多麻烦,但却给人们带来了乐趣,丰富了底层人民的文化生活。
《巍然屹立王者风范》
屹立在山坡上三千两百多年,送走过多少晚霞,迎来过多少朝阳,看惯多少兴亡事,历经了多少风暴雨狂,宏大的地球上,还有谁比它见多识广。
古人站大树前,曾发“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感慨,叹人生之短暂,岁月之无情。今我立树王前,更感造物之神奇,自然之佳妙,人生之有趣。能与三千二百岁老树共沐春光,同吸灵气,吾辈是何等之幸运,何等之快慰。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