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第二届“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以“渺小与苍莽”为主题,旨在挖掘关照现实、书写时代与个体,记录磅礴与幽微的优秀佳作。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七猫中文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上海作协担当指导单位,《收获》杂志担当文学指导,关注时代浮沉、家国命运、城市与乡村、女性叙事、真实罪案等众多题材,倡导以诚实的书写,展现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貌,理解自我与他者。
《玩乐时间:“六合彩”中的心灵与社会》作为“澎湃七猫特别奖”获奖作品,以地下六合彩为切入点,深刻揭示了社会特定群体在经济转型期的精神境遇和生活选择。文章基于丰富的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叙事手法独特,语言流畅,结构精妙,具有非常强的商业价值。
在近日镜相工作室发起的非虚构沙龙中,获奖者们分享了自身的创作故事,以下是作者欧椋的发言内容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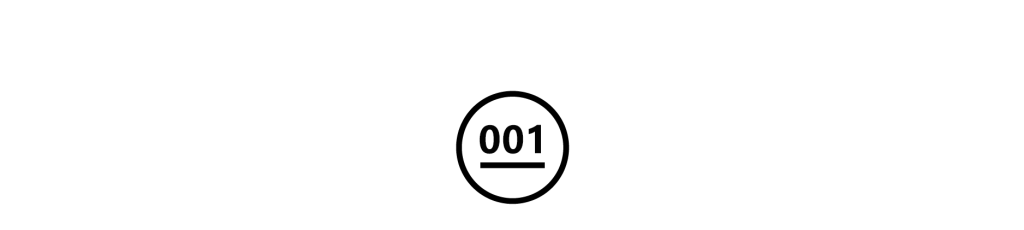
童年记忆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想写这个故事。实际上,我是教英语的,我很喜欢英语里的一个词——haunt,你可以试着念一下这个词,尤其是“n”的发音,会感觉嘴里含着一口气,就像空荡的房子里有个鬼魂在飘荡。
对我来说,因为我小时候出生在湖北的一个乡镇,目睹了许多长辈,甚至亲属,不断把自己的人生投注在荒谬的赌博游戏里。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家会愿意花这么多心力投身这样的游戏?我的文章里其实有很多篇幅在解释这个现象,这背后的行为逻辑到底是什么。首先,“特码之夜”,作为故事的开场情景,介绍了六合彩赌博游戏,大致是从1到49选一个数字,然后会有一个随机数字成为“特码”。如果你选中的话,赔率是1:40,所以有很大可能通过这个游戏实现暴富。这是我开头写的场景。我曾经亲眼见过这样的场景。人们围着所谓的“写单人”或“小马庄”,周围是镇民或村民,职业各异,大家都要找这个“马庄”下注。
接着,究竟怎么才能中奖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刚才前面提到,六合彩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游戏,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参考线索。由于它非常随机,当时就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说只要名字里带“天”字的电视节目,你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线索。
比如说,当时很流行看《天线宝宝》。我小时候有个任务,就是和我哥哥一起数《天线宝宝》里太阳出现了多少次,出现多少次就会对应一个数字。所以虽然听起来像是很荒谬的事情,但大家都非常激动地参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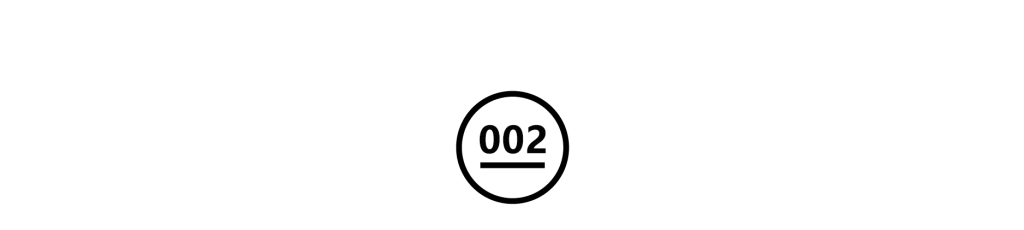
六合彩的魔幻现实
有一本关于六合彩的书,像考研参考书或者《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那样的大全,观察里面的目录你会发现,它虽然是地下彩票,是灰色地带,但它的设计非常精妙。比如说,其中包含了一些文化资本,诸如中国传统的紫薇八卦等内容,它都有所涉及。同时,它会在其中安排一些关于性的元素,或者幽默段子,来吸引底层群体的注意力。同时,它还有极强的商业头脑,会设计出像迪士尼那样具有人格化特征的形象,如白小姐和曾道人,用来吸引参与者的持续投入。
它太随机了,其实这是一个包含了许多阐释元素的游戏。归根结底,还是人们在其中根据各种文化线索进行自己的阐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有一种叫“码报”的东西。它会以女性的身体作为特码或玄机的载体,这里涉及到对女性身体进行神秘化塑造。
这种现象是跨历史、跨文化的。六合彩这种赌博游戏,它一方面借用了我们自古以来对女性、身体的神秘化处理,增加玄机自身的神秘色彩。另一方面又不断将女性身体性化,使其变成谜团。
小时候像这种印刷刊物,通常会通过印刷店发放,像发报纸一样送到每家每户。其实小时候我也看过这样的刊物,就放在我爷爷的桌上,可以随手翻阅,所以它已经渗透到小朋友的日常生活中。接下来的章节主要讲的是它如何渗透到时空之中。

“六合彩”如何重塑生活
因为六合彩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在观察人们赌博的时候,往往是在一些日常生活场景中,比如在厨房里,或者在小卖部。有的人把自己的小卖部白天用来卖东西,晚上则改造成一个临时的赌博场所。
除了空间上的影响,还包括时间上的影响。因为六合彩大概是在晚上8点半到9点开奖。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打电话给庄家,他可能会生气,因为这个时间段任何来电都有可能与当天要开什么号码有关。对我来说,我的观察是,这种活动对时空观的影响非常明显。我打了一个比方:它把人的生活变成藕节状的生活。我在文章里用到了很多农业化的比喻。藕节是一块一块的。人们不断地投入到这种每期开奖的游戏中,就会丧失对未来长远规划的能力和意愿,而是不断想着:下一期我要翻身,我一定会中特码。这样整个时间观念和人生规划就因此改变了。
其实下注这个行为是人类学一直喜欢研究的话题。比如格尔兹研究巴厘岛斗鸡,任何彩票其实也是一样。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当天晚上开什么号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乡镇版的“公共领域”。就像18世纪公共领域的诞生一样,大家在讨论时会参考自己的文化,像斗鸡一样进行展示和炫耀:比如说,炫耀自己知道某个号码和《红楼梦》有关,或者和以前的一段历史相关,人们会为它赋予各种自我解释。
这个过程,也是男性占据主导位置的一个过程。但这同时又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结构,但同时又进入了一个阶层的真空。在这个真空中,并不会完全因为你的性别或者阶层而获得话语权,更多要看你的战绩,以及你是否曾经压中过。

为何沉迷?
以我刚刚讲到的格尔兹对巴厘岛斗鸡的研究为例,他认为整个赌博游戏其实是对社会结构的模拟。每一个角色承担的风险和责任都是不一样的。以“码民”和“携带人”的关系为例,码民和携带人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附近关系”。码民会在自己熟悉的街道或者街区寻找携带人下单,一切都以信誉为基础。另外,这个生态系统里还有一些边缘角色。比如说中介,或者印刷店,他们也可以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此外,人们在赌博时的心理是我最初特别关注的话题:为什么你会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投入进去?
结论是,有时候人们赌博不是为了赢得这个游戏的胜利,而是为了能够继续参与这个不断前进的旅程。这样可以让人对日常生活感到满足,但对长远的未来却失去了激情,只是想停留在这个过程中。
最后,我还是想向大家介绍一本对我自己非常重要的书,就是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他其实讲的是,工人阶级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可以说,小镇居民一方面受限于现实条件,不得不选择进行这样的经济行为,试图改变自己的人生。但同时,由于他们自身某些特质,比如自己营造出的小镇文化,又不得不把自己限定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所以,总体上,我想引用的就是保罗·威利斯所表达的这个观点。
(编辑:柳逸;整理:沈益希)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