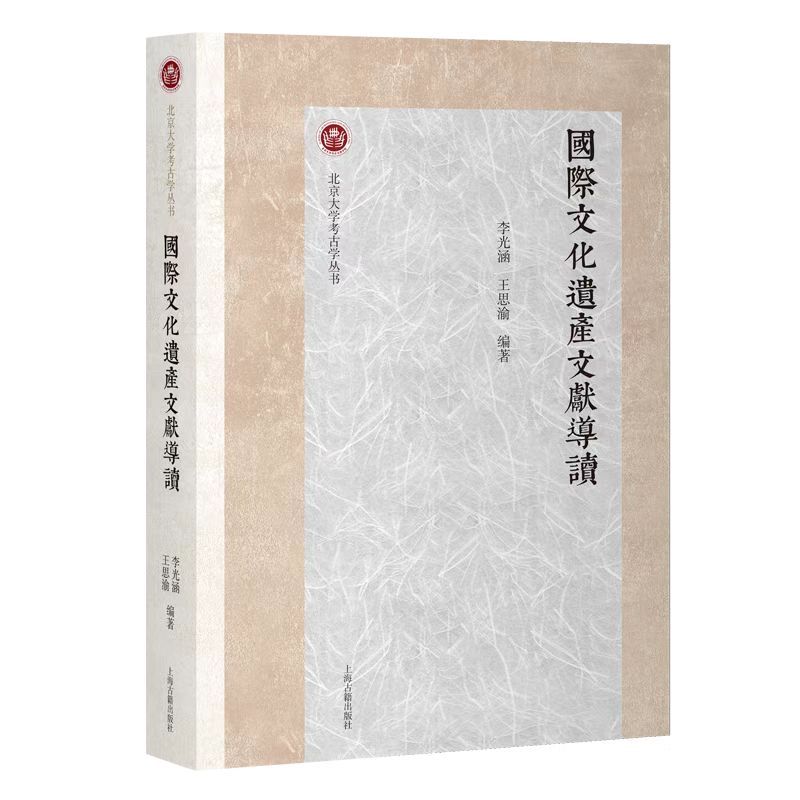
《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导读》,[新加坡] 李光涵 王思渝 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4月
我的专业是考古,1998年去上海博物馆工作之后,开始接触公众,这些年来考古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萦绕在心,所以几年前我看到罗德尼·哈里森的著作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的时候,就组织一些在校学生进行了翻译,即202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这本书的前言《遗产无处不在》提出了一些我们关注的问题:
难道没有别的比“过去”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吗?把遗产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现象考察,我希望不仅能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世界遗产公约》以来遗产与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变化,同时也表明,遗产最重要的不是关乎过去,而是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
现在,北京大学两位青年学者李光涵、王思渝组织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一批青年学者撰写了《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导读》。编著者在编后记中说:编辑初衷是“作为长期在高校从事文化遗产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者,日常中我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是,文化遗产研究是一个学科吗?”在现在高校的考核压力下,他们关注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遗产无处不在,又与现在、未来发生着关系,按照常理,遗产相关的研究应该在高校中受到重视,因为只有高校及时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才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社会中的人才需求。
中国高校中的遗产研究最初脱胎于考古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大规模基本建设中考古工作的需求,考古专业人才奇缺。1952年北京大学在历史系下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考古专业,并在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办了四期考古人员短训班,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了一批亟需的人才。改革开放后,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国内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山西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陆续创办考古专业。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独立建系,这个时期基于田野发掘的考古工作仍然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点。经过几十年的积累,2013年,考古学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逐渐成熟。随着国力的增强,除了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之外,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博物馆的展示阐释、与当代社会的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了我们的目前,这些均不是传统考古学研究的内容。高校学科建设受到学科评估的强烈影响,而学科评估评的是那些比较成熟的学科,但是现实社会中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却会因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比如文化遗产由于没有成熟的学科体系,年轻学者的文章很难找到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这是造成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脱节的表现之一,在此情境下从事遗产研究的年轻学者在高校不得不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导读》的编者认为:“‘文化遗产研究’能否成为一门成熟乃至独立的学科的问题,至少需要回答,这门学科能够解决哪些已有的学科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它契合的是怎样的时代发展需要?”基于此,他们编选了国际文化遗产学界四个方面的经典著述,第一部分便围绕着“价值与保护”,介绍了李格尔、勒杜克、卡博纳拉、布兰迪的保护理论;第二部分便围绕着不同的遗产类型而展开,这些遗产类型是随着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的深入而扩展出来的;而今天意义上的“保护”已经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已经不是,也不可能再是纯粹书斋里的学问,展示阐释、活态传承、社区参与、文化旅游乃至文化经济,都已经成了今天的保护运动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使遗产的话题更有批判研究的需要。
《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导读》读后使人思考良多。书中介绍的第一部著作是李格尔的《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正如标题所示,对古物的现代崇拜确实说明它并不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传统,虽然我们能够把对古物的收藏追溯到很远,收藏意味着喜欢,但喜欢还不是崇拜。这种崇拜带来了不同的保护理论和保护实践,所以,“保护”是伴随着西方现代性成长起来的概念,并随着“二战”之后的国际化协作的开展,在全球推广开来。
勒-杜克参与了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他认为“修复一座建筑并非将其保存、对其进行修缮或重建,而是将一座建筑恢复到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曾存在的完整状态”,这种观点自然会引起激烈的讨论(从这一点来说,编选者应该对拉斯金的理论予以介绍)。我也一直在想:勒杜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修复理念?他是不是在构筑一种建筑风格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中国建筑师对民族建筑风格的追求,这样一个层面进行思考,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勒杜克的做法,虽然在不同的建筑师眼中,民族风格是不一样的,梁思成有梁思成的做法,贝聿铭有贝聿铭的设计,但是他们心中其实都有一种“执念”。
布兰迪是遗产保护理论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布兰迪基于高雅艺术作品展开的修复理念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已经“过时”,但是其跨学科思考联结了形而上的艺术哲学与形而下的材料世界,仍然是我们思考艺术作品必须思考的方向。在《和卡尔米内论绘画》中,布兰迪认为:“艺术作品,是人类为了超越自身短暂存在而付出的最高努力,通过抵达永恒中的不变之法,使人类自身从时间中获得解脱。”
在我看来,艺术品的创作与宗教活动具有相似性,宗教是人类构筑神圣世界的活动,艺术也是。只是布兰迪认为:“这种努力一旦实现,作品本身就脱离了创造者之手,它被封装起来,成了完成时态,从(生成)中获得解放,然后被持续不断地拉向接收它的当下意识。”为了解释清楚艺术作品的这种特征,布兰迪引用了杜威的美学论证:“一件艺术作品,无论多么古老或经典,只有当它活在某些人的个体化经验中,才实际上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不仅是潜在的艺术作品。”在我看来,艺术品肯定存在于人的个体化体验当中,但是,它的艺术性同样存在于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建构中,概言之,我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并且通过国家、社会、个人不同的层面,与当下发生着联系。
世界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使得更多的遗产类型被纳入研究和保护的视野。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六届大会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遗产学界对文化线路长期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的总结性成果,《宪章》厘清了文化线路的概念和内涵,中国丝绸之路、长城、大运河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在我看来,文化线路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如果说大运河、丝绸之路构成“路”,长城并不是“路”,讨论这个方面的内容,可能还要涉及线性遗产和线状遗产,比如明代为了抗倭而在沿海地区修筑了许多卫所城,这些具有军事防御性的城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但又没有一条直接的交通线将其串联,联系它们的更多的是支撑它们的腹地城镇和聚落。
书中第四部分编选的批判遗产的几篇文章具有足够的批判性。美国学者大卫·洛文塔尔于1985年出版的《过去即异邦》一经出版,便立刻引起了英美人文学界的广泛关注。1992年10月31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便邀请洛文塔尔参加一场以“过往即是异邦”为题的辩论会,可见其学术上产生的影响。书中值得探讨的论题很多,重新回到李格尔的《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这种崇拜导致“遗产无处不在”,甚至在2014年,库哈斯出版了一本名为《保护正在压倒我们》的书籍,宣称“当下几乎没有办法来与我们巨变和滞胀并存的未来谈条件”。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产生这种崇拜,甚至发展出一种压迫感呢?我想其实源自人类灵魂深处的焦虑和呐喊。随着现代性的产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的灵魂追问就没有停歇过,对遗产的保护其实是人何以为人的探究,在0和1构成的怪兽在人类面前越来越有压迫感的时候,我们需要回望过去,重新构筑我们的神圣世界。如果说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精神家园,那么就可以说:
过去并非异邦
遗产即是故乡
杭侃
2025年4月16日于山西大学
(本文系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导读》所作序,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