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澎湃·镜相”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以“渺小与苍莽”为主题,特设奖金池33万元,旨在挖掘关照现实、书写时代与个体,记录磅礴与幽微的优秀佳作。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七猫中文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学术、创作、出版、影视界的多方代表共同参与评审,从选题、信息和文本等多维度考量,最终评选出12篇极具潜力的非虚构作品,并将继续推动出版和影视改编等多种形式的内容开发。
《桐树下》(作者:吴桂凤)获此次大赛一等奖,以下内容为获奖作品节选,“镜相”栏目独家首发,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四月的一个清晨,早起,窗下看书。夜里下过雨,有风清凉、自窗外田野漾漾而来;鸟儿叫得欢快,一声声,清脆鲜亮。我以为我又回到了童年家中,正是初夏时节,有豆叶青青。每天在晨曦中醒来,洗漱完毕,搬了小板凳去顶楼阳台晨读。待太阳从大榕树后升起,阳光洒在房前竹林间、洒在我膝头的书本上时,我便合起书,收拾起小板凳哼着歌儿下了楼来。妈在备早餐,晨光中,厨房里白气腾腾,有葱油煎水豆腐,新摘下的豆叶煮得喷香......妈呀,闻得我都饿了。帮妈洒扫地板,擦洗灶台、饭桌,摆碗筷,盛好一家人的饭,一个一个喊叫来围坐着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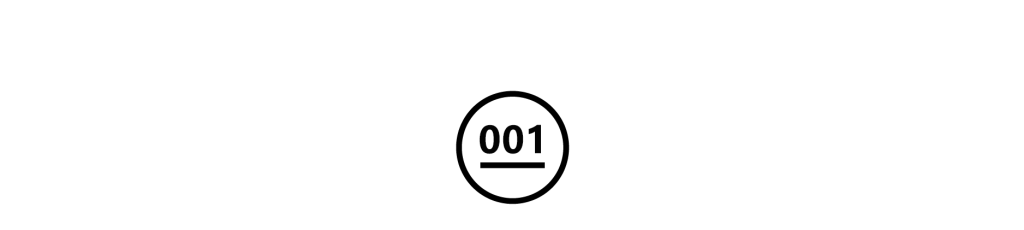
出生
我家在桐树下。四围都是山。一脉又一脉山峰绵延,山上遍植松树、杉树,也遍布着祖先坟墓。山脚下一条公路东西朝向,去县城、市区往东走,朝西去往镇上。公路下面一片田,田里终年种植着庄稼。公路往北豁一口,便是村道入口,近处一条小溪,溪水淙淙,东西蜿蜒而下。溪两旁绿竹成林,四季青绿,竹丛下常有烧尽的石炭灰铺就堆作肥料春夏之交便会有尖尖的绿竹笋“噗噗”地冒了出来,又有鸡们在石炭灰上蹲坐成窝打盹儿。溪上横两根木头搭作桥,供村民来往,终年经风历雨,木桥上青苔湿润,蘑菇丛丛,常有孩子趴桥上惊喜地找拔小蘑菇玩耍。桥下沿岸随意散布些个石墩石板,用于人们淘米洗衣,逢年过节杀鸡拔毛。过了桥,遍是一座座土楼围屋错落分布,泥墙青瓦杉木小门窗,傍晚时分家家屋顶上炊烟袅袅而起,锅碗瓢盆筷“铿铿”作响,阿姆(客家话,念作mei,第一声,指妈妈)们呼唤孩子回家吃饭声此起彼伏......一个无名无闻的小村庄,村庄里住着几十户吴姓人家。这里没出过名人,没出过进士,更没有富商大贾大官大儒,甚至医生、律师、教师、警察这样吃公家饭的人都没有,唯有两个小学教员,还是民国时期生人。只有一代一代平凡无名的村民,动物一样生,植物一样长,遵循着不知从哪朝哪代传下的规矩习俗,在世间劳作扑腾几十年,作一碗饭食,留下几个后代,或贫或病或老默默死去,抬山上埋了,松树、杉树林下多一个坟墓,了事。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凉透了的秋,我出生在这个村庄。
妈说,那时稻谷已收割完、入了谷柜;稻秆晒干捆扎收起进杆棚;花生也收晒完装了箩筐储存;新买的鸡仔也已养熟,天黑识得跟随大鸡入笼......这时,她发现腹中胎儿有了变动,便知她的第二个孩子要出生了,赶紧挑了畚箕去山坡上挖番薯,此时不挖,等生下孩子坐完月子,番薯早烂在地里了。
寂静的午后山坡,风吹高大松树“飒飒”响,妈一个人滚圆着大肚子锄头掘地挖番薯。阵痛一阵紧一阵,她越挖越慌,怕孩子生在这荒坡野岭。馺霎(客家话,快快)挖完回家,把番薯理净、进窖;把猪圈里的猪喂饱;把家事通通收拾妥当,匆匆清洗了身体,爬到床上,等待孩子出世。爸下班回来,妈让他赶紧去喊接生婆。接生婆还没到,我像个小动物般出世了。妈挣扎着探起身,一看:又是个女儿!心都寒了!随便扯了个薄被单遮盖那光溜溜、血淋淋的小动物,灰冷着心等爸请来接生婆。
生下当晚我啼哭不止。抱着哭,抱着来回走着哭,放下躺着哭,喂奶不吃、尽着哭,哭声凄厉,哭得爸妈慌了,不知将要发生啥。爸说:“不晓得这小东西能不能养大。”随手拢了床厚绒毯把那坨小东西紧紧搂在怀里。立刻便止了哭,想必是生下那会儿光溜溜薄被单遮着,无人问津,受了冷受了晾。
我就是这么被期待、却让人失望地出生的。每次听妈讲起这段故事,心中总是愤愤:知道要生了,还去挖番薯,不怕把我生在山坡上么,不怕我生下来冻死么,不怕招来邪灵把我带走么,不怕黄鼠狼把我叼走么,这么个寂静的山坡,一个人也无,除了风吹松树“飒飒”响,除了一个一个的坟墓。然而,此时的愤愤干预不了当时的无奈。在那个贫穷压倒一切的80年代,人们为了生存已用尽全力,钝感比敏感容易活下去。生下来能不能活下去各凭本事,活不下去那也只能由着自然的结果死去,天生地长,最不缺的,就是人了。
生下了,便得养大她。因为又是女孩儿,奶奶不待见,板着脸摔东掼西照顾妈妈坐月子。妈心里堵,咬牙熬过了半个月就不要奶奶照顾了,自己挣扎着起来照料家庭,照顾不到2周岁的姐姐。不到一个月妈便下地了,手上牵着姐姐,背上背着我,落水洗裳,下地栽种,肩挑手提,手脚麻利。年长些的嫂嫂婶婶见妈这样劳做,好意提醒:“杀头嫲,做嘛个不识得保养自己,坐月便这般劳作,会落下病根,老了有得苦食。”一面翻开大红花色小被单看看里头裹扮着睡得香喷喷的小女婴,啧啧夸赞:“诶哟,哈正板,哈正板,水色子哈靓(jiang,第一声,客家话,漂亮),奶水哈好。”又夸赞一旁跟着的姐姐,也被妈喂养得圆滚滚。天气晴好的时候,阳光暖融融,微风拂面,天地的爱意似比亲妈还亲,妈把背上熟睡的小女婴解下来放田埂上睡,大红花色被单一半垫着一半盖着。姐姐自己在地里玩耍,摘花折草刨草根,天地广阔由着她撒欢儿。瞧瞧碧蓝蓝的天、明灿灿的日头,黑的土、绿的草、青碧的妈栽种的菜、大红花色的被单、被单里熟睡的粉白色的小妹妹,姐姐叫着、笑着、奔跑着,一会儿一会儿跑去看一下妹妹。
一天一天,日子就这么过着,我也一天一天长大,会“呀呀”说话了,会站了,会走了,会跟着姐姐玩儿了。小鸡仔也在长大,羽毛渐丰渐润,“唧唧唧”跟在母鸡后面啄食。我跟在姐姐后面看妈喂鸡,也学姐姐的样子抓一把谷子在手里喂给鸡吃。一头大雄鸡,火红的冠子,斑斓的羽毛,长得比我还要高大,挺拔着身子趾高气昂走过来,吓得我扔了谷子抱住妈的腿大哭。妈一脚踹得那大雄鸡“嘎嘎”叫着扑着翅膀跑开了,又骂着大雄鸡,说话安慰我,却已弯不下身去抱我,我长大了,她的肚子挺得跟我一般大,里头又有一个小人儿,不晓得是弟弟还是妹妹。
没多久,妈生了,又是个女孩儿,小小一只,浑身黑红黑红,皱着脸。爸的脸也皱着,不说话,卷着烟丝、擦亮火柴、抽烟。妈擦眼泪、发愣。许久,爸吐出嘴里的烟雾,说道:“送人吧。”妈同意了。实在是太穷了,计划生育抓得又严,在村里生产大队当干部的邻居已经不止一次告诉爸妈,大队随时会来抓人去结扎。而爸妈,还想生个弟弟,因为必须要有一个儿子!
妹妹送人了。姐姐留在家给奶奶,爸妈带着我东躲西藏。外婆家,远房亲戚家,废弃柴房,深山煤窑洞......天地之大,总容得下一对想生孩子的夫妻和他们年幼的崽,可以容身就行,可以遮风避雨就行。
天寒地冻的一天,妈撑着大肚子,一手提着提兜,一手牵着嘴里鼻孔里哈哈出气的我回到了家。爸为了多赚钱下了煤窑,妈先回来待产。家里门窗桌椅全是灰尘,窗上挂着的蜘蛛网在寒风里牵扯,灶是冷的,锅碗瓢盆散落各处,姐姐顶着鸡窝一般枯黄的头发拖着两行绿浓鼻涕咬着通红的手指看我们。妈叫:“巧儿,巧儿。”姐姐眨了眨眼,喊了声:“姆......”两行眼泪浪浪而下。妈给姐擦眼泪,自己擦眼泪。紧忙着生火烧水给姐洗脸洗手换洗衣服,把房屋收拾清洗打扫一番,家又热气腾腾活了过来。
妈生了。还是妹妹。从煤窑赶回来陪妈生产的爸一句话没说,和十二月的寒风一道用力把门刮得山响,又回了煤窑。妈眼睛肿得像发粄。奶奶在楼下对着天骂,对着屋顶骂:“人也生,你也生,人一个一个都生儿子,你生的都什么晦气东西,一藤一串!这么冇(mou,第二声,没有)用,怎么不去死!怎么不去死!”妈把妹妹抱起又放下,抱起又放下,牙齿咬得打颤:直接把它从楼上摔下去给奶奶完事儿!终究是忍下了,奶疼。自己的命自己受,孩子有什么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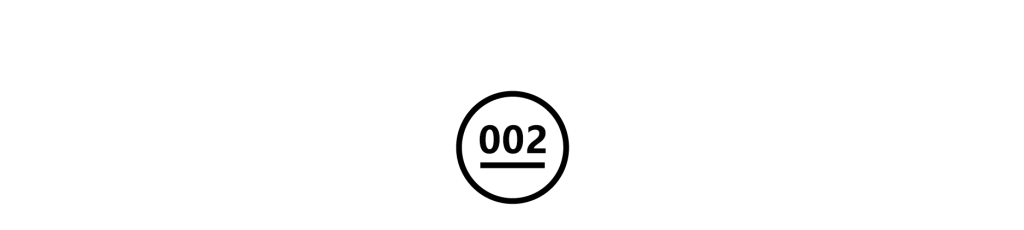
爸,妈,不要把妹妹送人
开春了,田里开始松烟地、种烟草,妈一个人忙不过来,爸从煤窑回来帮忙。夫妻两个,三个女儿,一群鸡,一圈猪,这么一大片烟地,还有马上要春耕播种水稻,每天早出晚归,累得腰折。还有,穷,钱不够用。爸妈商议着,不能再生了,养不起,一定得有一个男孩儿,那就换一个吧,女孩儿换男孩儿。
托人介绍了一户人家,家里有三个儿子,想要一个女儿,愿意换一个。于是,来家里看人。姐姐5岁,是长女,不能送人;我4岁,清秀乖巧,一对眼睛亮晶晶灵透了;妹妹粉扑扑,还抱在妈妈手上,吃喝拉撒都需要照料,还费人工。爸妈把姐姐、我和妹妹收拾一番,穿上过年的新衣裳,事先教我和姐姐如何叫人如何应答。他们一眼看中了我。用最小的儿子换我,比妹妹还小,还费人工。爸妈没有选择的条件,只能同意,还要贴他们120元,因为他们家的是男孩儿。
择了吉日,那户人家备了礼品,抱了男孩儿,来家里换我。家里乌洋洋都是人。爸妈准备了香烛炮要拜天地神明祖宗,请来了亲朋,邻居......要摆酒席,用嫁女儿的礼仪送我出门,毕竟养育了一场。还要120元。爸妈低着头拨开人群去楼上拿这笔巨款。5岁的姐姐紧跟着爸妈上楼,一面哭一面说:“满(客家话,爸爸),满,他们说要把我们的凤妞儿送人,是不是真的?”爸给姐擦眼泪,说:“不是真的。”“满你骗人,(ngai,第二声,我)都看见了,他们拿红包给凤妞儿,没给和小妹妹;姆姆(mei,第一声,妈妈)给凤妞儿穿了新衣裳,没给和小妹妹穿。”姐抽抽噎噎数落着种种不平迹象。爸哽噎了脖子,说不出话。“满,我们不要把凤妞儿送人......不要换弟弟......满,他们的弟弟那么丑,才不要,只要自己的妹妹......”姐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鼻涕抹了一脸,眼睛都睁不开。爸妈翻箱倒柜在找钱,抽屉、衣柜、床柜、壁柜,衣服口袋,每个藏钱的角落都翻遍了,翻不出120元,姐姐哭得他们崩溃了,爸眼泪滂沱,搂住姐姐,说:“不换,不换,他们那些人歪心肠,乱讲的,没把凤妞儿换弟弟。”爸给姐姐擦了眼泪,跟妈说道:“不换了!一般般都是人,我们的会行会走会打酱油,他们还抱在手上,多费人工,我们还要贴钱给他们。不甘心!不换了!苦死也要养大她们。”
大人多苦,我和姐姐不懂。不过有一回,我看见爸哭了。那天夜很深了,土楼围屋静悄悄没了人声,都睡熟了。爸还没回来,妈点着煤油灯做针线等爸,姐姐的裤子膝盖上绽了一个洞,妈在给她补裤子。灯光投下妈的身影把整个房间都罩住了。姐姐和妹妹睡得“咻咻咻”,冒着热气。妈以为我也睡了。我困极的,爸没回来我不放心,闭着眼听外面的动静等爸。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地,听到敲门声,妈去开门销,一阵风刮进来,爸倒进房间。爸喝醉了。妈插上门,去扶地上的爸。爸哭了,压抑着声音,嘴里说着“太苦了......”、“撑不下去了......”含混不清。妈低声喝止爸:“你冷静些,邻居听见笑话。灌嘛个马尿!灌这半夜三更,吞醉了好好去睡,哭什么!看孩子给吵醒,吓着她们。”爸这么大人了,为什么还哭?我咬着被角,心紧紧的,揪在一起。妈把爸扶到床边,我害羞让爸妈知道我看见爸哭,紧紧闭了眼用力装睡,然后便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仍旧和姐跟在妈身边,快快活活地,养猪、喂鸡、种菜、洗衣裳......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每个都那么新鲜有趣。就说喂猪吧。一大镬猪食煮得热气腾腾,把剁好的番薯叶倒进去,再舀一瓢谷糠下去,搅拌一下,糠香混合着番薯叶的味道弥漫厨房。妈背上背着小妹妹,手上一瓢一瓢把浓稠的猪食舀进木桶,我旁边眼睛不眨地看着,不自觉舔了嘴唇:这香,不晓得啥味儿!猪食舀完,妈洗锅蒸饭,我从门后拿了担杆给妈,她挑起猪食桶去喂猪。一开猪圈的门,三头欢蹦乱跳的小猪便争先恐后挤了过来,谁也不让谁,簇在石槽边“嗷嗷”叫。妈才舀起一瓢猪食,小猪们便粗鲁地把长嘴巴凑到瓢里乱拱,“吭哧”“吭哧”叫着,把瓢也拱翻了,伴着一两声尖锐的猪叫,不晓得烫着谁了。妈一脚踹了近旁的那头猪,骂道:“瘟鬼,慌死作嘛!”我和妈背上的小妹妹“咯咯”笑个不停,学着骂猪“瘟鬼”。看妈喂猪的结果是,每次吃饭要剩饭时,妈只要说浪费食物下辈子要做猪,我怎么撑也要把饭撑下去,那么憨顽贪婪的猪,我不做的!我要做人。做人有那么多好玩儿呐,还有那么可爱的小妹妹。小妹妹也会走路了,我和姐姐牵着她走得跌跌绊绊,成了我和姐姐每天最大的乐趣。妹妹还会叫我们“阿阿”,我和姐姐抢着疼她,玩到哪儿带到哪儿。
寻常的一个圩日。妈背着妹妹和邻居婶婶去赴圩,交代我和姐姐乖乖在家,等她买“等路”回来我们食(等路,客家话,礼物,父母去赶墟或探亲访友或出门在外回家时,给老人、小孩带回一点饼干、糖果之类的小食)。我和姐姐在门口泥坪上玩。四方形土楼围屋围起一个大天井,泥坪地,是我和姐姐的乐园,也是鸡鸭们活动的地方。阳光从天井上空一泻而下,晒得泥坪地结结实实,暖暖和和。我和姐玩累了,躺泥坪上看天井上蓝悠悠的天,心也蓝幽幽的,活着多么好哇。突然听到六六嫂和伯母在讲悄悄话:“嘿呀,听讲要送人家,早就讲好了,今天带去圩上给人。”我和姐翻身爬起来,跑过去问:“六六嫂,谁送人?把谁送人?”六六嫂叹气道:“还有谁!你老妹啊,你妈背去圩上送人了。”我眼泪翻滚下来。我不信。才不信呢,爸妈从没说要把妹妹送人啊,我们那么喜欢妹妹,妈怎么会把她送人呢。她们肯定乱讲的。爸常说这些婆娘子们没事就喜欢乱讲别人闲话。可是,我和姐不玩儿了,坐门槛上,心神不宁,等妈回来。
妈终于回来了。可是,妈背上的妹妹呢?妹妹怎么没了?我和姐奔过去,顾不上她买回来我们爱吃的发糕、苞粟。拽着妈的衣角,闹嚷着:“姆,妹妹呢?她们说你把妹妹送人了。为什么要把妹妹送人?不要把妹妹送人。”嚷着嚷着我和姐姐大哭了起来。妈把我们牵回家,给我们擦眼泪,平静说道:“没有把妹妹送人,她们乱讲,骗你们小孩子的。”我和姐将信将疑,睫毛上粘着眼泪,问:“那妹妹呢?怎么不见了?”妈说:“赴圩时,在圩上遇见外婆,她说想妹妹了,要把妹妹带回去看几天,过几天看够了就送回来。”噢~我们都很喜欢的外婆呀。我和姐姐信了,不再烦恼,翻那些“等路”,嘴里叮嘱妈:“那过几天一定要把妹妹带回来啊。”“嘿呀。嘿呀。”妈应着。
从此,妹妹再没回来。

“流浪汉”
妈被抓走了。爸没说为什么。每天沉着脸,早出晚归赚钱。我和姐姐小心翼翼,怕触怒爸。我难过了,妈还没生弟弟呢,没弟弟怎么行,爸妈那么渴望弟弟。过了两天,妈回来了。他们说她是偷跑回来的。妈顾不上管我和姐姐,一回来收拾了包裹和爸一起又走了。
我和姐姐成了“流浪汉”,不知饥饱不识冷热。奶奶呢?奶奶可不管我们,她说照顾孩子太累,她做不动,她只每日搬了小凳子坐别人家门口陪人说话晒太阳。奶奶煮了饭,我和姐姐就吃;没煮饭,就饿着,反正怎样都能活着,头发还长得特茂盛,如杂草疯长。我和姐姐不会梳头发,皮筋胡乱捆扎散乱着,满头长着了虱子,静静躺着时能听到它们在蠕蠕爬动汩汩吸血的声音,痒得我狰狞暴躁,头皮都抓流血了。“这荒草丛生的日子啊,无知无明的生活,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我的悲伤突然从洪荒而来,不由对着天空放声号啕。我一哭,姐姐也忍不住哭了,我们俩哭得掏心掏肺,无人问津。我家斜对门有个老太太,妈平日里教我们喊她“伯婆”,八十几岁,拄着拐杖颤巍巍走了来,手抖抖地递给我们两颗西瓜糖,一面安慰我和姐:“莫哭,莫哭,你们的妈妈会回来的。”我和姐住了哭,接过糖,糖饧了,糖纸被溽得皱巴巴,光摸着便知道很甜。我和姐脸上挂着泪,目呆呆地看着她。老太太用枯瘦得只剩下皮的手给我们抹眼泪,那手刮得我脸疼,粗沙子似的,她手上的老茧太厚啦。实在哭得太累,我们嘴里噙着糖,泥坪地上倒下便睡了,不管地上鸡屎鸭屎苍蝇漫天漫地。老太太又拄着拐杖颤巍巍走来,拿了件衣服盖在鸡屎鸭屎苍蝇堆里睡着的我和姐姐身上,自语:“可怜这两个冇爷娭(客家话,父母)管的细妹子。”
我和姐姐不知哭了多少回,泥坪地上睡了多少天,老太太给我们盖了几回衣裳,只知道妈走的时候,老太太给我们盖的是单衣,后来给我们盖棉衣,再后来棉衣上还加了一层小绒毯。突然有一天,爸妈回来了。妈把我和姐从鸡屎鸭屎泥坪地上叫醒,我们揉着眼睛混混沌沌以为在做梦。妈忙着打扫、收拾家,我和姐牵着妈的衣角一叠声嚷:“姆头佬,你和满满去哪里了,怎么都不带我们去......”一面嚷着一面眼泪又流下来。妈烧了水给我和姐姐洗头发,换了一盆又一盆的水,洗了一遍又一遍,还篦了一盆底的虱子。妈的眼泪像竹丛下的雨后溪水,湍急汹涌......
妈总归是回来了。我和姐有了着落。和小伙伴玩耍时,傍晚炊烟下喊回家吃饭的呼唤声里也有了我和姐姐的名字:“巧儿——凤儿——,转来食饭啦......”“巧儿!凤儿!'儿'也喊得出口,带把儿了吗?就喊'儿'!有这面(客家话,脸)!”背后的言语传到妈的耳朵里,妈咬紧牙牵着我和姐的手急急往家走。那些老婶婆,那些大伯姆,那一张张丑陋的老脸,浑浊的眼睛!我和姐一路翻白眼怼还给她们。妈怕她们,我和姐才不怕!她们的孙子——健狗子,培老牯,烨老轱......哼,男孩儿又怎样,他们玩游戏,全都玩不过我。刚才跟烨老轱玩锤子剪刀布,他输了我多少下鼻子,要不是我故意轻轻划一下了事,他那塌塌的肉鼻子准得被刮成包子。哼~~他还不服气呢,约了明天再玩。
第二天,我正帮妈择菜呢,妈当昼(客家话,中午)要做芋头煮粉干,得用葱头起油锅爆得香香的才好吃。我咽了咽口水,一抬头,烨老轱在我家门口探了探头。哈,他真来了。妈不让我和姐跟这些男孩子玩,免得淘气惹了是非,可姐还是常跟他们打架,闹得鸡犬不宁。我不打的,我力气小,打不过。菜择好了,我跟妈说我要去拉屎,于是顺利溜了出来。烨老轱在凉棚下等我。我问他:“今天比什么?”
烨老轱说:“比锄草。”
“锄草?”我疑惑。凉棚旁是培老牯他们家的猪寮(liao,第二声,客家话,猪圈)。猪寮旁散乱堆着一堆石头,缝隙里,泥土里,到处是杂草。蝴蝶在翩飞,鸡在啄草,猪在寮里吃食,大家各忙各的事,我为什么要跟他比锄草?那又不是我的事,那是大人干的活儿呢。
烨老轱轻蔑冷笑:“哼,你不会了吧?不敢吧?臭女孩子,胆小鬼!”
“你才胆小鬼!你更臭!比就比。”我转身回家去拿锄头。烨老轱直接从培老轱他们家猪寮旁拿好锄头等我。
锄头太重了。我才5岁,手扶着把手柄倒立地上,锄刀朝上,足足高出我一个头。烨老轱也5岁,跟我一般高,但是他天天吃肉,壮实得很,一身蛮劲儿。他也把手柄倒立地上,锄刀朝上,站我对面跟我讲比赛规则。锄头太重啦,我手抖了起来,手臂酸软无力,把不住了,手一松,锄头倒下,直接栽向祺老八的头。
一声惨叫,一股殷红的血从烨老轱的头上流出来。身旁黑压压立刻围满了大人。烨老轱他爸冲进人群,头发眉毛肩膀全竖了起来,一巴掌劈头扫过来,扫得我踉踉趄趄,站立不稳。他眼睛眦裂,眼珠爆突,用食指一下一下狠狠地戳我的额头,戳得我头发散乱下来,一面厉声骂:“绝种嫲!我烨老儿要有什么事,拿你的命来赔!有人生没人管的绝种嫲,拿你十条贱命都不够赔!”
妈拨开人群走近来,一面打我,一面哭,一面跟他们道歉,又一面跟众人分辩“这么小的孩子......”我呆呆站着,脑中一片黑暗。叫声,骂声,哭声......像海水滔天汹涌而来,铺天盖地要把我淹没了......到胸口了,到脖子了,要没顶了,我要死了......“啊——”我捂上耳朵,惊恐大叫,转身飞跑,心里有声音急切地喊:“快跑,快跑,海水淹上来了,快跑,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你带我走啊,妈妈,我不要留在这里,我好害怕......”
我要跑去哪里呢?到处是荒草丛生,没有人。躲起来,快躲起来。他们追来了,他们要我的命。出村口的村道上两排都是房屋,屋檐下反扣着人家的板车。我从侧缝里钻进去,蹲在地上瑟瑟发抖,从板车床的竹片缝隙里看人们来来回回奔忙的慌乱的脚步......他们没发现我,他们没发现我,我安全了......
醒来时,我怎么躺在家里的床上?清晨的一束阳光从松木窗棱穿射进来,新鲜又明亮,斜斜地落在床上,被子上,我的脸上,眼睫毛上,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束里漂浮翻滚,我伸出手,要抓住这一束阳光。姐姐喊我:“凤妞儿,你醒了?”我应她:“阿阿。”姐姐说:“你昨夜把我吓死了,睡梦里又哭又叫,满满姆姆都止不住你。”我头枕在枕上,闭了眼,认真想,什么也想不起来。姐去把妈叫来。妈端来一碗蛋花汤,喂我热热喝下去,是甜的,妈放了糖。吃完,妈问我昨天和烨老轱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昨天淹没我的海水又汹涌来了......我大叫一声,把刚吃的蛋花汤全吐了出来。妈不问了,从此再也不让我跟烨老轱玩,我们两家也不再来往。每回远远看见烨老轱的爸爸,我都绕着走,怕他刀子一般要割我肉的眼光。而烨老轱的大伯茂老子,回回看见我都朝我吐口水,骂一句:“绝种嫲!”
(作者:吴桂凤;编辑:柳逸)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